第二篇 台湾共产党的演变与毁灭(1928—1932)
第四章 第一次破坏与党的重建(1928—1930)
对所有在日本控制地区下的共党而言,一九二八年是悲惨的一年[1]。
日本当局对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使得共党的领袖日趋谨慎。事实上,经过「三一五事件」后,日共遭遇了严重损失,但上海的日警并没有松弛对台共的监视,他们多次大逮捕的行动使得新成立的台共受到惨重的打击。
第一节 台湾共产党第一次被破坏(1928年4月)
(一)上海台湾读书会事件
正当台共建党准备期间,林大顺、翁泽生、谢雪红三人纠集上海台湾学生会左翼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的主要成员包括江水得、杨金泉、林松水、刘守鸿、张茂良、陈粗皮、陈美玉、和黄和气等人,他们致力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和中共党员也保持联系,尤其特殊的是,他们还与朝鲜共党份子组成联合战线,这些活动引起上海日本领事馆的注意[2]。
在朝鲜人庆祝「三一革命运动」□周年时,张茂良与许多读书会分子参加了纪念会活动,并发表声援文。日本人因此得悉台湾人的秘密活动,他们也获得情报,知道林木顺要成立一个秘密团体,这使得日本人决定采取逮捕行动,以了解事情的真相[3]。
上海是一个国际性都市,当时在各种不同的势力控制之下,但代表这种势力的不同国家间有某种协调,以维持公共秩序。这种协调使得日本人能在不同的处所完成三次成功的行动,第一次是三月十二日发生在不属于共同租界的闸北,由于中国治安当局的协助,日本人逮捕了黄和气、江水得、陈美玉。第二次行动是三月三十一日,在共同租界逮捕了陈粗皮。最后一次发生在台共建党大会后十天,张茂良、杨金泉、林松水、刘守鸿、谢雪红等人在法国租界被日警逮捕。
这个时候台共所有的重要文件都已被查扣[4],尽管缺乏实质和正式的证据,我们相信这同时发生在日本和日本之外的逮捕行动,必然互有关联[5]。在被逮捕的九个人当中,陈美玉被判断与这件事无关后获释,其余八人被解送回台湾接受侦讯[6]。
在审讯期间,黄和气和谢雪红以证据不足获释[7],一九二九年四月三十日,其余六人以组织秘密团体,「目的在要否认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权,及废止一切的私有财产制度,以建设共产社会」[8]等罪名,违反治安维持法而提起公诉。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高等法院判决杨金泉、张茂良二人两年徒刑,其余四位分别判处两年徒刑,缓刑四年[9]。
(二)党员的逃亡和日本人控制的强化
震撼台湾政坛的上海台共事件告一段落之后,因为主要人物林木顺、翁泽生、谢玉叶(翁妻)仍然在逃[10],日本当局继续监视,并且保持警戒。当时,谢雪红这名台共的主要组织者已经落在日本当局手里,但是他们并未发现她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同时她的智慧也足以应付审讯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当局在逮捕行动后,认为他并未接触到台共核心的原因[11]。
无论如何,在幼年期的台共这次受到严重打击,损失了几位预定的干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建党大会采用的计划不能遵行或要加以修正的原因。林日高参加建党大会后由上海返台,五月十五日会见了三位缺席获选的委员庄春火、洪朝宗以及蔡孝乾,告诉他们台共成立的经过以及党所采用的政策。
上海读书会事件后,由于感觉危机日增,他们决定暂时停止活动以等待机会[12]。建党大会后由上海返台的潘钦信、谢玉叶二人偕同蔡孝乾、洪朝宗,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底秘密搭船离台,前往福建。蔡孝乾逗留在漳州和厦门一带继续推展活动,并与上海方面保持联系,直到一九三二年他进入「江西苏区」[13]为止。潘钦信也一直留在厦门,一九三〇年他返回上海并遇见翁泽生[14]。蔡孝乾和三位同伴逃亡中国大陆的行动,据蔡孝乾的解释是为了避免党在台湾完全被毁灭[15]。
基于日本政府控制力加强的观点,蔡孝乾为党的生存而逃亡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项逃亡的决定正好指出,建立在知识分子上的台共组织先天的脆弱性,诚如首批党员陈来旺的说法:
「……由知识分子指导的党,一个百分之百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在白色恐怖的袭击下,就会引起机会主义的动摇,……一听到检举,就协议逃亡,竞相放弃工作并逃往日本和中国。一受到压制,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机会主义就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由此事实证明,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党是如何的无力!」[16]
逃亡在中国的党员是应该回台湾工作的,而突然回台的谢雪红却应该留在岛外以保持与日本方面的联系,这个组织上的变动台共并未事先安排,这种事实状况以及随后蔡孝乾等四名党员的行动,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但也引发了内部的斗争。在逮捕共党分子之后,日本政府在其本土及国外都加强了治安上的措施,以强化对各种左翼运动的控制。治安维持法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修改后,加入死刑的处罚[17],这个法律早在一九二五年便已施行于台湾[18]。一九二八年七月,东京警视厅扩充特别高等警察为全国性的组织,由内务省集中管理,以便监视各地的社会运动。
成千的特务人员因此被派往本国各地区工作,并与各地区地方警察密切地合作,他们的情报都送往内务省处理。台湾和朝鲜的民族运动同样□被称职的官员监视着,上海、伦敦、海参崴等国际都市都在这些官员的监视下,特别受到注意的是颠覆运动和煽动分子[19]。
基于同一理由,台湾总督府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建立一个特别高等警察体系,从台湾总督府到地方行政各个阶层,这些特高警察负责监控所有的左翼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台湾和其它地方的航运交通也因此加强了[20]。这些作法后来成为渡边政之辅在台湾死亡的起因,后文将会讨论到。
第二节 东京特别支部的成立与破坏(1928年9月—1929年4月)
(一)特别支部的成立
台共在上海建党时,曾经做出成立东京特别支部的决定,这个事实一方面反映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在日本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示台共想强化日共对台共的指导。因此,特别支部的成立在于加速共产主义运动,并扩大对台湾人的影响力,同时,借助特别支部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特别关系,可以从日本本土开始向台湾渗透共产主义的势力,以完成殖民地获得解放的「国际任务」。
陈来旺前往上海参加台共建党大会后,「东京台湾青年会」下的「社会科学研究部」——左翼台湾学生组织——由于受到日共「三一五事件」的影响,改变名称为「台湾学术研究会」,并暂时停止活动。四月二十三日陈来旺返回东京以后,携回建立台共支部的任务。尽管当时形势已经变化,他仍然和原有同志联系,并为东京的台湾共产党运动进行组织上的筹备工作[21]。
一九二八年八月,逃避上海四月逮捕事件的台共书记林木顺抵达东京,他带来日共中央委员会有关台共建党和随即被破坏的报告。在东京他与陈来旺碰头,双方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并决定建立东京支部应采取的步骤,陈来旺推荐两位台湾学术研究会的积极分子林兑及林添进入党[22]。
九月二十三日晚间,陈来旺、林木顺、林克及林添进四个人聚在一块筹备东京特别支部,由陈来旺负责。在会议中,他们决定了两项任务[23]:
1.在「台湾学术研究会」和「东京台湾青年会」建立党的指导地位,以便吸收台湾学生为党员。
2.建立与日共以及台湾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关系。
林木顺是由党派定回台的党员,因为安全的理由放弃了回台的计划,十月底他回到上海,重新加入翁泽生组织上海台湾人的行动行列[24]。
在重整后的日共指导下,台共东京特别支部的活动日趋积极[25]。一九二八年年底以前,在陈来旺的拟议下,学术研究会内的委员会成员于东京文化协会下的《台湾大众时报》社址集会三次[26],这些成员包括林兑、萧来福、黄宗葵、何火炎、陈铨生、林裳、苏新和陈来旺,他们讨论了组织的指导路线和活动内容,其中重要决定如下[27]:
1.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台湾人。
2.改革东京台湾青年会,使它在东京特别支部指导下成为一个大众团体。
3.出版一份报纸。
4.组织一个台湾人联盟,支持《無產者新聞》。
5.组织一个支持委员会,以援救从事台湾解放运动的受难者。
6.对即将在一九二八年年底召开的台湾农民组合大会发表声援书。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陈来旺、何火炎、苏新、萧来福、林兑、林添进、李清标、林加才、黄宗葵等人举行支部会议,他们将七个地方小组重组为十个学校小组并分配各人的任务。他们决定加强征募党员以及销售《無產者新聞》的工作。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学术研究会的活动有所进展,青年会的左倾会员也逐步被吸收。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青年会的一次聚会中,在「学术研究会」会员的领导下大会通过改革青年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日本台湾学生会」,当日选出的委员会成员几乎全是研究会的会员。青年会在特别支部的指导下改组,成为东京台湾人的左翼组织[28]。
(二)特别支部被破坏
自从特别支部在学术研究会和青年会中建立领导地位后,支部藉这两个组织扩展自己的活动,并与台湾的左翼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底,林兑被支部派往台湾,携带支部的指示和林木顺准备的“農民問題對策”[29]。一九二八年夏天,林兑趁着假期返台,和农民组合领导人之一的简吉联系,并和当时在台湾着手重建党中央的谢雪红取得联络。他们共同指导台湾农民组合第二次大会,这次大会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举行,结果强化了台共对台湾农民运动的影响力。林兑拒绝出任农民组合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返回东京[30]。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日本当局开始逮捕台湾农民组合的干部,农民遭受了惨重损失,东京特别支部派遣学术研究会的主力分子返台,以协助农民组合的再建运动。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事件前夕,日共组织的领导人间庭末吉被捕,从他身上捜获的日共党员名单给日警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并据以发动一九二七年以来的第二次大逮捕行动[31]。在这份名单中有三位台湾人,为了知道这三位台湾人的名字,东京警察逮捕了四十三名台湾学术研究会的主要会员,因为这个组织早被视为左翼台湾人的组织。在侦讯中发现了陈来旺、林兑、林添进的日共党员身份而加以逮捕,其余人则以证据不足获释,但仍遭日警严密监视。
特别支部于存在了六个月之后,遽然被破坏而告消失,但是在逮捕行动前返台的苏新、萧来福、林朝宗以及逮捕行动后返台的庄守,继续在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些学术研究会的成员尝试重整会务,在这些尝试证明无效后,这批旅居东京的左翼台湾人一个个转向日本左翼文人的文艺活动中去了[32]。
第三节 党中央在台湾成立(1928年11月)
上海台湾读书会事件对台共而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谢雪红获得释放,却开启了台共一个新的局面。
(一)恢复活动并与日共联系
谢雪红自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获释后即返回台中家乡。从一九一四年台中人士争取设立台中中学开始,这个城市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一九二七年,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分别将其大本营自台北和台南移至台中,使得台中成为台湾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中心。
谢雪红并不了解被破坏后党的实际状况,尽管如此,她决定继续进行她的活动,在她返回台中后,重新参与文协与农组的活动以便寻找干部并与党员恢复联系。她一方面准备党在台湾的重建工作,另一方面推展台共在文化协会和农组中的影响力[33]。不久,林日高返回台中与谢雪红取得联系,他们交换有关情况的意见,并检讨五月十九日蔡孝乾、洪朝宗等人得错误决策——有关停止活动以及逃亡中国大陆的决定。他们决定由林日高前往东京与日共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并听取有关恢复党员工作的新指示。在抵达东京后,六月二十日林日高在《大众时报》与东京特别支部负责人陈来旺会面。但是因为三月十五日事件后,日共及日本左翼组织受到严重的损失,特别支部与日共的联系暂告中断。林日高和陈来旺决定等待下去,八月,林木顺由王万得[34]陪同由上海抵达东京,四人曾经数次集会,检讨台湾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林木顺最后任命林日高先行返台,等候日共新指示,之后他也返回台湾。
八月底,林日高返台并携回林木顺给谢雪红的命令,依照命令,他们应该遵照建党大会采用的决议以及「政治大纲」内规定的任务,进行党的活动。
(二)党中央委员会的成立和渡边政之辅的死亡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日共的新指示传抵台湾,谢雪红召集林日高、庄春火在台北家中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委员会议。依照日共新指示,谢获选为中央委员。三人做了下述决定[35]:
1.蔡孝乾、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四人放弃职务逃亡中国,应开除这四位机会主义者的党籍。
2.吸收杨克培、杨春松为新党员[36]。
3.分配中央委员会职务:
书记长兼组织部部长——林日高
劳工运动部兼宣传煽动部部长——庄春火
其余事务负责人——谢雪红
由于林木顺未如约返台,而林日高虽被任命为台共书记长,但事实上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谢雪红手中。因此,由林木顺担任书记长的台共第一阶段至此宣告结束。
他们决定由谢雪红和杨克培在一九二九年年初开设「国际书店」,一方面贩卖左派读物并宣扬左派思想,另一方面也作为党的集会场所。在日警的严厉监视下,新的中央委员会为了生存而隐蔽起来,而利用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的活动场合来强化党的影响力[37]。
谢雪红经常返回台中,保持与文协和农组内同志的联系,她又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有关土地问题、抗日及无产阶级运动等的讨论会[38]。
由于这些努力,她才能从文协和农组中吸收党员,并在这些组织中建立台共的支部组织。基于党的方针,谢于一九二八年八月提出三份有关青年部、妇女部以及救济部的组织「提纲」[39],这三份提纲稍后为农民组合中央委员会所采用。
一九二八年年底农组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谢雪红联合林兑企图在农组中建立党的领导地位。林兑这名东京特别支部的党员,其返台主要是传送书记长林木顺有关“農民問題對策”的指示。虽然大会遭日警解散,党中央却在第二天秘密发布一份取材自“農民問題對策”的声明[40]。
台共逐步地渗透农民组合内部而影响它的活动,日本当局不得不有所反应。他们决定不再允许农民组合公开传布共产主义,使农村受其思想毒害[41]。日本当局以农组分发宣传品违反出版规则为由,发动大规模的搜索行动,总共捜索了三百个支部和房舍,超过五百人被逮捕,农组领袖简吉、杨春松、陈德兴、陈昆仑、颜石吉、张行、苏清江、江赐金、侯朝宗、谭庭芳等被捕处缓刑[42]。「二一二事件」,日警虽然未能证实农组与台共的关系,但这个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却给农组及左翼运动严厉的打击,台共被迫更审慎地进行活动[43]。
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警察对停泊在基隆港的「湖北丸」轮船进行检查,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日本。检查中发现一位谷物商的证件不合规定,又在他的行李中发现大批外国证券。谷物商在行将被押往办公处所时拔出左轮枪,枪击日警成重伤之后企图逃亡,最后在警察包围下举枪自杀。内务省的调查报告中显示,这个涉嫌人事实上是日共新书记长渡边政之辅[44]。渡边是日共的领袖,他和建党后的台共有密切关系,自从逃避东京三月十五日逮捕事件后,他来到了上海并与林木顺碰面,听取林木顺有关台共状况的报告。无疑的,他和日共中央委员会曾经拟出台共未来的指导路线,他很有可能携带对台共的重要指示而来台。日共刊物曾指出,「渡边同志前往台湾,负有重要的任务。由于不能逃脱危险,他毅然自杀以保护党」[45]。以后,某些台共党员悲痛地回忆:假如渡边能够安抵台湾,台共后来的活动将演变成另一种局面[46]。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文件能说明渡边来台所负任务的真正性质[47]。
渡边的死、一九二九二月十九日农民组合干部被逮捕,以及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事件后东京特别支部被破获等事件,切断了台共和日共间经常性的联系。由于各种事件的影响,造成台共的困扰与问题,台共党员们发现自己已陷入孤立地位。除了借助于长驻上海的联络员寻求中共的帮助和第三国际的指令外,台共没有第二条路可行。
第四节 党的更生运动与松山会议(1930年10月27日至29日)
(一)党的更生运动
台共中央委员会当时由谢雪红、林日高、庄春火三人组成,在一九二九年年初以前,只空有这个领导机关,缺乏坚强的实质组织,也没有几个党员。但是,两位候补党员苏新和萧来福在日本四月十六日逮捕行动前,已应东京特别支部派遣回台,庄守也在被释放后返回台湾[48]。此外,居住在中国大陆参加中共共青团的王万得、吴拱照、刘守鸿也相继返台,并成为台共党员[49]。文协和农组的成员也陆续入党,不仅增加了党员的数目,同时也增加了台共的影响力。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逐渐萧条,各地的无产阶级运动也逐步获得进展,这种情势对停滞不前的台共发展相当有利[50]。
一九二九年十月,谢雪红、林日高、庄春火在国际书局集会,讨论当时的局势并重新分配职务,他们做了以下的决定[51]。
1.指定地区负责人——
台北市:王万得
基隆地区:苏新
高雄地区:刘守鸿[52]
2.指定左翼组织台共支部负责人——
文化协会:吴拱照、庄守
农民组合:杨春松、赵港
3.重新分配中央委员会职务——
宣传煽动部:谢雪红
劳工运动部:庄春火
组织部:林日高
由上面的工作指派可以看出,台共已展开全岛从南到北的活动,并强化台共对左翼组织的控制力量。日本在二月十二日对农组干部及成员的压制,增加了农组成员对台共的同情与依附。因此,农组中的党支部也增强了活动,党的控制地位逐步建立[53]。文协中的党支部同样地也建立了领导地位。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文协第三次大会开幕时,连温卿——这位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日共党内丧失主要地位的山川主义派忠实信徒——的力量已被围绕在王敏川周围的「上大派」所超越,终于遭到文化协会的除名。至此,台共在文协的领导权也确定了下来[54]。
一九二九年年底,台共已经控制了读书会和青年会等组织,并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工作——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方面,以便从中征募党员。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组织日益扩展,依照一九三一年逮捕台共事件后日警的调查,当时已有十七个与台共有关的组织,其中大多数在谢雪红的影响下活动[55]。
为了确保党的发展,台共对于所谓的右翼改良主义的团体,如「台湾民众党」以及由民众党分裂出去并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另外成立的温和派「台湾地方自治联盟」,采取了批斗和反对的态度。在台共的领导下,文协、农组及左翼工会的干部在文协彰化支部集会,组成「打倒反动团体斗争委员会」,以巡回演讲的方式「谴责」并「揭发」右派改良主义者。这样的活动聚集了相当数目的支持者[56]。
台共党员同时出版杂志:包括谢雪红、杨克培、郭德金出版的「台湾阵线」,王万得联合周合源、陈两家、张朝基和江森钰等五人合创的「伍人报」[57],由于日本检查尺度甚为严厉,所以实际上都被禁止出版。
(二)松山会议
自从加强在台湾的活动后,台共又寻求与外界恢复联系。因为考虑到没有机会和日本联系,日共和台共东京特别支部当时仍在日警的压制下无法活动,所以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台共决定派遣林日高前往上海,透过翁泽生与第三国际联系。林日高直到一九三〇年四月才离开台湾,他取道厦门与潘钦信、谢玉叶两人取得联系,五月抵达上海与翁泽生见面。翁泽生不满意台湾的台共活动,他说:「台湾的党几乎是离开大众,没有活动表现,目前不过只是一个研究的团体,必须要做根本的改革」。而且,「台湾的客观情势已有显著的变化,党的各种工作方针必须重新检讨」[58]。翁泽生要求林日高提出书面报告,以便向第三国际东方局详细报告台共的活动情形以及台湾的局势。林日高完成报告后留在上海等候上级的指示,直到七月底才有人告诉他,要他先行返台,上级不久之后将派员赴台传达指示。林日高失望之余于七月返台,向谢雪红提出脱党声明书。庄春火也跟着退党[59]。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激进的」年轻党员日渐增多,这批人感觉党的领导力不足,同时对中央委员会的不满也逐渐扩大转为不信任,当时党中央委员会仅有谢雪红为代表,她遂成为众矢之的[60]。林日高和庄春火脱党后,谢雪红逐渐感到孤立,其间也因为第三国际的指示久候不至,她感觉需要党内有力分子支持,王万得正是她所信任的人选。
与王万得讨论之后,谢雪红在松山召开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会期从一九三〇年十月廿七日至十月廿九日,参加的人员包括杨克煌、吴拱照、苏新、赵港、庄守、王万得等人,他们决定了一条党的临时指导路线。
谢雪红指出党不能有所发展的原因[61]:1.日本当局的压制,2.党员的消极态度,3.中央委员会的被动态度。王万得分析了台北地区劳工运动的状况,赵港和吴拱照分别就农民组合和文化协会的活动提出报告,庄守和苏新提出他们对南部和北部地区工会运动的看法。有关工运的报告,批评党对于工会组织运动缺乏一定的方针,放任党员个别行动,造成工运停滞不前。最后会议做成以下的决定[62]:
1.任命指导劳工运动的负责人——王万得及苏新。党应该确立一条指导路线,以团结工会组织。
2.建立或扩大农组支部,使它们成为独立的组织,并准备参加未来的「赤色总工会」。
3.文协已无工农分子,实际上已成为小市民阶级的大众斗争团体,党应该改变它的组织性质。
4.开除林日高、庄春火的党籍,中委缺额等下次大会再予补全。
松山会议一方面决定了党的临时指导路线;另一方面,党领导机关的不健全和指导力的薄弱也展现在党员代表面前。处于孤单情势的谢雪红被削弱领导权,党员感觉到需要一条更实际的指导路线来面对台湾的情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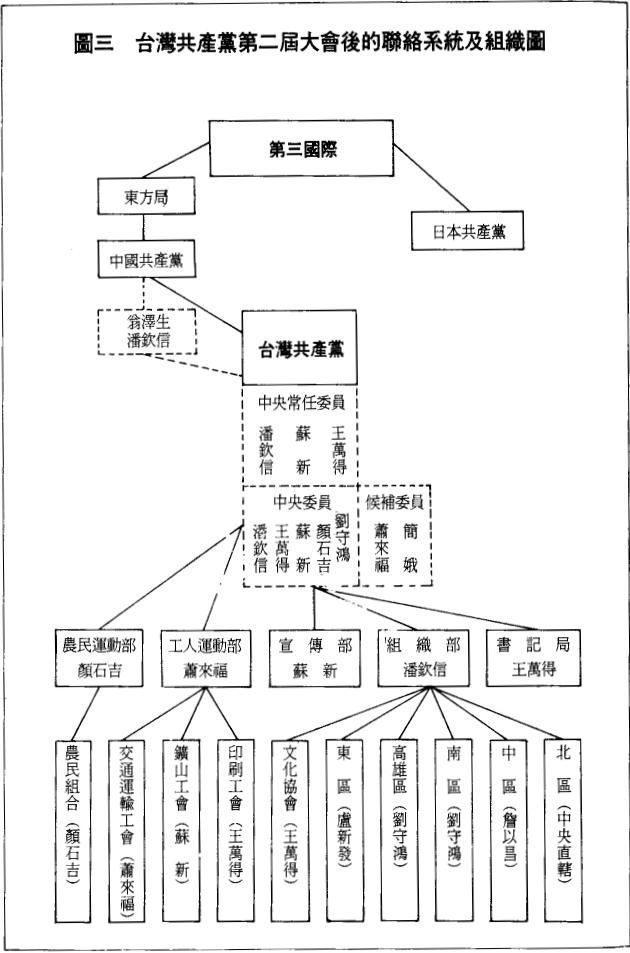
[1] 治安警察法及治安维持法先后实施之后,警力大为扩张,对于左派运动造成极大的打击与损失,此种情形让人觉得日本根本就是一个警察国家:"……the Japan of late twenties, under its parliament, was basically a police state", Cf. Reger Swearingen et Paul Langer, Red Flag in Japa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Action, 1919—1951(New York:Greenwood Press, 1968), pp.31—32.
[2] 参阅(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编,《臺灣共產黨の檢擧槪要》(东京:1928),收入:《臺灣II》,页237—238。以下简称《臺共檢擧槪要》。《沿革誌》,页86、661。
[3] 《沿革誌》,页661—622;《臺灣II》,页237—238。
[4] 《沿革誌》,页662;《臺灣II》,页244—245。
[5] 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如佐野学、渡边政之辅、市川正一、山本悬藏等人均逃过了「三·一五大检举」。Cf. Scalapino, p.34.
[6] 《臺灣II》,页245;《沿革誌》,页662。
[7] 《台共秘史》,页29;《沿革誌》,页662。
[8] 《台湾民报》259期,1929年5月5日,页3;宫川次郎,《臺灣の社會運動》,页328—330。
[9] 宫川次郞,同上。
[10] 《臺灣II》,页245。
[11] 《沿革誌》,页663。
[12] 同前注。
[13] 蔡孝乾,《江西苏区……》,页1—3;E. Snow, p.103.; H. F. Snow, pp.324—325.
[14] 《沿革誌》,页673—674。
[15] 蔡孝乾,同上,页3。
[16] 陈来旺,“臺灣の黨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收入:《臺共檢擧槪要》附录,参见:《臺灣II》,页271—273。这是陈来旺根据在台党员提供的资料,向日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1929年4月27日东京警察在市川正一住处搜捕时发现这篇报告。
[17] Swearingen et Langer, p.32.
[18] 黄静嘉,页132。
[19] Swearingen et Langer, p.32—33. 立花隆,上册,页255—258。
[20] 井出季和太,第二册,页849—850。
[21] 《沿革誌》,页43、664,另参阅:“陳來旺聽取書”,收入:《台共檢擧顚末》,见《臺灣II》,页87—88。
[22] 林兑,台中人,日本大学商学系三年级学生。他在台北师范学校就读时,曾参加1924年10月由三年级学生组织的罢课行动,反对日本人的教育歧视,因而被开除。次年,他前往东京继续求学。参阅“林兌聽取書”,收入:《臺共檢擧顚末》,见:《臺灣II》,页101—102。林添进,台中人,情形和林兑相同,也到东京求学。参阅“林添進聽取書”,收入:《臺共檢擧顚末》,见:《臺灣II》,页111—112。
[23] 有关成立东京特别支部的讨论内容,参阅陈来旺、林兑、林添进的审讯记录,见:《臺灣II》,页87—88、103、112。
[24] 《沿革誌》,页664、813。
[25] 参阅“陳來旺聽取書”,见:《臺灣II》,页90。
[26] 文协分裂后,台湾民族运动唯一的机关报《台湾民报》仍在旧日干部的控制下,这些干部离开文协后,另外组织台湾民众党。1928年3月,文协在台中成立《台湾大众时报》,但没有获准在台湾发刊,因此将报社迁往东京,于5月7日创刊发行,经由秘密管道送回台湾。由于困难重重,1928年7月9日《台湾大众时报》出版第10期后,便停止发行。参阅《沿革誌》,页219—220。
[27] 《沿革誌》,页43—45。
[28] 青年会的改组系以「读书小组」为基础,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参阅宫川次郎,《臺灣の社會運動》,页340—347。另参阅“東京臺灣靑年會通信”,见《臺灣II》,页214—228。
[29] “林兌第二回聽取書”,见:《臺灣II》,页109—111;及“陳來旺聽取書”,见:《臺灣II》,页91。“農民問題對策”此一文件和台共建党大会所采纳的“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同样重要,但主要部份更为具体简要,有助于重建台湾农民组合,使之变为「赤色」农民组合,全文请参阅《臺灣II》,页156—164:《沿革誌》,页1088—1098。
[30] “林兌第三回聽取書”,见《臺灣II》,页108—109、111。
[31] Swearingen et Langer, p.37.
[32] 《沿革誌》,页49—67。
[33] 参阅“臺灣共產黨事件”,页2;《抗日篇》,页158。《沿革誌》,页667、1071。
[34] 王万得,台北人,是文化协会领导人之一。1927年1月前往中国大陆,在武汉加入中共。1928年3月,他前往南京从事活动。参阅叶荣钟等,前揭书,页351;《台共秘史》,页35。
[35] 《沿革誌》,页668—669。
[36] 杨克培,彰化人,1927年由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前往中国,在武汉成为中共党员。1928年8月,杨克培回到台湾,由谢雪红介绍加入台共。参阅《台共秘史》,页37—38。杨春松,新竹人,是农民组合中央委员。参阅《沿革誌》,页1085。
[37] 《沿革誌》,页669;“臺灣共產黨事件”,页2。
[38] 谢雪红在台中农民组合的所在地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1928年底,除了谢雪红之外,重要成员是简吉、陈德兴、杨克培。参阅《沿革誌》,页669。谢与农民组合合作,举办问题讨论会,讨论有关青年、妇女、农组的策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批判殖民政策等等的问题,参阅《抗日篇》,页158。
[39] 参阅“台湾农民组合青年部组织提纲”,见《沿革誌》,页1072—1073;“台湾农民组合妇女组织提纲”,见《沿革誌》,页1073—1076;“台湾农民组合救济部组织提纲”,见《沿革誌》,页1076—1078。
[40] 参阅《沿革誌》,页1071—1072、1084—1085、1087—1088、1098—1099。“林兌第三回聽取書”,见《臺灣II》,页109—111。参阅“農民問題對策”,见《臺灣II》,页156—164;及《沿革誌》,页1088—1098。有关“台湾农民组合第二次全岛大会宣言”,参阅《沿革誌》,页1099—1101。
[41] 叶荣钟等著,前揭书,页534,未注明出处。
[42] 《台湾民报》239期,1929年12月29日,页2。宫川次郎,《臺灣の社會運動》,页368—371。
[43] 《沿革誌》,页669、1102—1103。叶荣钟等著,前揭书,页534。
[44] Cf. Swearingen et Langer, p.36.
[45] 《沿革誌》,页669—670。
[46] 同上。
[47] 日共在其党史中,始终声称渡边被警察「谋杀」。但是到了1972年,却改口说渡边是自杀的。参阅:立花隆,上册,页297—298。根据Beckmann & Okubo,渡边到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台共的组织发展(参阅页171)。但是,他们对此种说法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
[48] 苏新,台南人。1928年10月,他成为东京特别支部的候补委员。参阅《台共秘史》,页39;“臺灣共產黨事件”,页2。萧来福,台南人,台共候补委员,《無產者新聞》台湾部门的负责人。1929年3月间,他返回台湾,同年10月成为台共党员。参见《台共秘史》,页40—41;“臺灣共產黨事件”,页2。“莊守聽取書”,见:《臺灣II》,页149。庄守,彰化人,1928年3月入早稻田大学,同年10月加入台湾科学研究会。萧来福返台后,庄守取代了他的地位,负责发送《無產者新聞》的工作。参阅《台共秘史》,页50;“莊守聽取書”,见《臺灣II》,页147—150。
[49] 吴拱照,新竹人,1928年5月在上海加入台共。由于加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被日警逮捕遣返台湾,判刑一年,缓刑四年。1928年11月8日释放后与谢雪红取得连络,受命参与文化协会的活动。参阅,宫川次郎,《臺灣の社會運動》,页332;《台共秘史》,页6243;《沿革誌》,页245。刘守鸿,于上海读书会事件中被捕,判刑2年,缓刑4年,1929年8月释放。他在国际书局工作,接受谢的指挥。参阅《台共秘史》,页49—50;“臺灣共產黨事件”,页2。
[50] 《沿革誌》,页670。
[51] 同上。
[52] 刘于1930年3月被派任这个职位。参阅《沿革誌》,页670—671。
[53] “台湾社会运动团体”,《台湾民报》294期,1930年1月1日,页8。另参阅:许世楷,页335—336。
[54] 参阅“台湾社会运动团体”,同上;许世楷,同上。连温卿派和王敏川派的冲突,反映了1927年后日本社会民主派人士与共产主义份子之间的对立。参阅山边健太郞的评注,见:《臺灣II》,页13—14。
[55] 参阅“社會科學研究會一覽表”,见《沿革誌》,页753—756。
[56] 《沿革誌》,页756—759。
[57] 《伍人报》,创刊于1930年6月,只维持了六个月。从第15期开始,改称《工农先锋》,不久与《台湾阵线》合并。《台湾阵线》创刊于1930年8月,但被禁止出版。12月改变名称为《新台湾阵线》,但始终被日警禁止发行。参阅,王一刚(即王诗琅)“思想鼎立时期的杂志”,《台北文物》3卷3期,1954年12月,页131—133。曹介逸,“日据时期的台北文艺杂志”,《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页47。另参阅:尾崎秀树,“决战下的台湾文学”,见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71),页207,注23。
[58] 《沿革誌》,页671的引述。
[59] 参阅《沿革誌》,页672—673。我们可以确定林与庄的脱党,一方面因为地下活动不断遭到日本的压制,另一方面由于翁的批评以及在上海徒劳无功的等待使林大为失望;此外,1928年4月,台共遭到第一次破坏时,林及庄显得颇无作为。谢在党中的领导地位也可能是促使林和庄脱党的原因之一。
[60] 郭乾辉(郭华伦),《台共叛乱史》(台北:内政部调查局,1955),页39—40。
[61] 《沿革誌》,页672。
[62] 同上,页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