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现象学,或关于辩解的学说
正如我们在“旧约的经济”及其后已经看到的那样,圣桑乔所论述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同庸俗的利己主义者,即“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混淆起来。相反,无论这后者(事物世界的俘虏、儿童、黑人、古代人等),或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思想世界的俘虏、青年、蒙古人、近代人等)都是他的前提。然而由于唯一者的秘密的性质,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即在新约中才来对这种对立和由此产生的否定的统一,即“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加以考察。
因为圣麦克斯想把“真正的利己主义者”说成是某种全新的东西,说成是过去全部历史的目的,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证明自我牺牲者,说教者是被迫的利己主义者;而证明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是自我牺牲的,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神圣的利己主义者,所以我们就从前者,从自我牺牲者谈起。
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乡下佬雅各的世界中一切人都是圣物的中迷者。“然而有教养者与无教养者”之间“仍有差别”。从事于纯粹思想的有教养者在我们面前表现为parexcellence〔再好也没有的〕对圣物“中迷的”人。这是实际形态的“自我牺牲者”。
“谁是自我牺牲者呢?当然〈!〉,完全的〈!!〉自我牺牲者大概〈!!!〉就是那个为了一个,为了一个目的、一个意志、一个欲望而把其他一切牺牲掉的人……一个欲望执掌着他,为了这个欲望他牺牲了其余的欲望。难道这些自我牺牲者不自私吗?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统率的欲望,所以他们所操心的也就是这一个的满足,因而也就对它照料得更加热心。他们的一切所做所为都是利己的,但这是片面的、不开展的、局限的利己主义;这就是中迷。”(第99页)
因而,在圣桑乔看来,他们只有一个统率的欲望;难道他们也应当为不是他们的而是别人的欲望操心,以便上升到全面的、开展的、非局限的利己主义,来适应“神圣的”利己主义这个外来的尺度呢?这里,他又顺便举出了“吝啬者”和“追求享乐者”(大概,因为施蒂纳认为他追求的是“享乐”本身,是神圣的享乐,而不是各种各样的实在的享乐),以及“例如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等”(第100页)来作自我牺牲的、中迷的利己主义者的范例。“某人根据一定的道德观点〈就是我们这位圣者,“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根据他自己的、与自己最不一致的观点〉大致这样来论断”:
“但是当我为了一个欲望而牺牲掉其他的欲望时,我并没有为了这个欲望就这样把我和使我成为确实是我自己的那种因素牺牲掉。”(第386页)
由于这样两句“不自我一致”的话,圣麦克斯被迫提出了一个“细微的”区别:尽管为了一个欲望也可以牺牲六个“例如”、七个“等等”的欲望而仍不失为“确实是我自己”,但是愿上帝保佑不要牺牲九个或者九个以上的欲望。的确,无论罗伯斯比尔或圣茹斯特都不曾“确实是我自己”,正如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曾确实是“人”一样,然而他们确实是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两个独一无二的人。向“自我牺牲者”证明他们是利己主义者——这是爱尔维修和边沁已经充分使用过的旧把戏。圣桑乔“自己的”把戏就是把“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资产者,变为非利己主义者。可是,爱尔维修和边沁是要向资产者先生们证明,他们目光短浅,实际上是危害着自己,而圣麦克斯“自己的”把戏却在于向他们证明,这些资产者不符合利己主义者的“理想”、“概念”、“本质”、“使命”等,并且不是作为自己的绝对否定来对待自己。这里,在他的头脑里出现的仍然是那个德国的小资产者。顺便指出,我们的圣者在第99页中是把“吝啬者”作为“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提出来的,相反,在第78页中他却把“贪得者”算在“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不纯洁、凡俗的人”里面。
对于这个第二类至此述及的利己主义者在第99页上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这些人〈资产者〉因此不是自我牺牲的,不是奋发的,不是理想的,不是一贯的,不是热情的人;这是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一心为己、枯燥无味、斤斤计较的自私自利者。”
既然“圣书”离开正题,那我们在“怪想”和“政治自由主义”各章中已经有机会看到,施蒂纳怎样主要地通过他对于现实的人和关系的完全无知才把化资产者为非利己主义者的把戏玩成的。这种无知在这里也是他的支柱。 “凡人的顽固的头脑与这一点〈即施蒂纳关于无私的臆想〉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凡人至少已被征服到这样的地步,即必须低下不屈的头颈并尊重更高于他的力量。”(第104页)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在行为中半像僧侣、半像凡人,他们既为上帝也为财神服务”(第105页)。
在第78页上我们读到:“上天的财神和地上的上帝二者都要求完全同样程度的自我舍弃”,在此,为财神而自我舍弃和为上帝而自我舍弃怎能作为“世俗的”和“僧侣的”自我舍弃而对立,是难以理解的。在第106页上乡下佬雅各向自己问道:
“然而那些主张个人利益的人的利己主义为什么总是经常要顺应僧侣的或教书匠的也就是理想的利益呢?”
(在这里应该顺便“预示”,资产者在这里被描绘成个人利益的代表。)这是因为: “他们自己感到他们个人太微不足道了——事实上也是这样,——致使他们不能奢望一切,不能完全伸展自己。关于这一点的无可置疑的证明就是:他们把自己分成永恒的和暂时的两个人,礼拜日操心的是那个永恒的人,平日操心的则是那个暂时的人。他们内心里存在着这个僧侣,因此他们不能把他摆脱掉。”
这里疑虑包围了桑乔,他担心地问道:独自性和非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呢”?我们将看到,这个使他担心的问题的提出是不无根据的。在公鸡还没来得及叫第二遍以前,圣徒雅各(Jacqueslebonhomme)将会有三次“舍弃”自己。
他非常不愉快地发现,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即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和所谓普遍利益,总是互相伴随着的。像通常一样,他发现这一事实是在错误的形式,神圣的形式下,从理想的利益、圣物、幻觉的角度去发现的。他问:普通的利己主义者,个人利益的代表怎么会同时受共同利益、教书匠的统治,而处于教阶制的权力之下呢?他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大意是:市民等等“感到他们个人太微不足道”,在这一点上他所找到的“无可置疑的证明”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他们把自己分为暂时的和永恒的人这件事;这也就是说,他先把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斗争变成斗争的幻相,变成宗教幻想中的简单反思,然后以他们的宗教信仰来解释他们的宗教信仰。
至于理想进行统治是怎么一回事,请看前面论教阶制的那一节。
如果把桑乔的问题从那种浮夸的词藻译为普通话,那末它“应该这样说”:
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像成为理想的,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桑乔哪怕有一天懂得这样一件事实,就是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只要他领会到这一点,那末至于把这一事实作为宗教去想像,还是在那个把统治着自己的力量都归结为观念的利己主义者的想像中被歪曲为无在他之上统治着他,他就可以比较无所谓地对待了。那末一般说来,桑乔就会从思辨的王国中降临到现实的王国中来;就会从人们设想什么回到人们实际是什么,从他们想像什么回到他们怎样行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行动的问题上来。他也就会把他觉得是思维的产物的东西理解为生活的产物。那时他就不会走到与他相称的那种荒诞粗鄙的地步——用人们对于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分裂也以宗教形式去想像以及用自己是这样的或那样的觉得(这只是用另一词代替“想像”),作为对这种分裂的说明。
但是,即使根据桑乔从中体会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的那种荒诞粗鄙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形式,他也应当看到,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因此桑乔指出的两个方面就是个人发展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同样是个人生活的经验条件所产生的,它们不过是人们的同一种个人发展的表现,所以它们仅仅在表面上是对立的。至于由发展的特殊条件和分工所决定的这个个人的地位如何,他比较多地代表矛盾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是更像利己主义者还是更像自我牺牲者,那是完全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内对一定的个人提出,才可能具有任何一点意义。否则这种问题的提出只能导致在道德上虚伪骗人的江湖话。但是桑乔作为独断主义者,在这里却发生了错误,他只找到一条出路:那就是宣布桑乔·潘萨和堂吉诃德之流降生,而使堂吉诃德之流在桑乔之流的头脑中塞进各色各样的蠢东西。他作为独断主义者抓住事情的一面(他是以教书匠的精神去理解它的),把它硬加在个人的头上,而对另一面则表示厌恶。因此,在他这个独断主义者看来,就是这另一面也部分是简单的精神状态,dévo?ment〔自我牺牲〕,部分只是“原则”,而不是个人以往的自然形成的生存方式所必然产生的关系。所以,也只有把这个“原则”“从头脑中挤出去”,尽管根据我们桑乔的思想,这个原则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经验的实物。例如,在第180页中“生活和社会性的原则”“创造了”“社会生活,一切社交活动、一切友爱亲善和其他……”其实反过来说更正确些:是生活创造了这个原则。
对我们这位圣者来说,共产主义简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因此,共产主义者并不像圣麦克斯所想像的以及他的忠实的Dottore GraziaNo〔格拉齐安诺博士〕(阿尔诺德·卢格)随声附和的(为此圣麦克斯称他为“非常机智而有政治头脑的人”,“维干德”第192页)那样,是要为了“普遍的”、肯牺牲自己的人而扬弃“私人”,——这是纯粹荒诞的想法,关于这一点,他们二位就在“德法年鉴”里也已经可以获得必要的解释。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突出的地方正在于:只有他们才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此,我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对立面的“否定统一”,而是过去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由物质所决定的消灭,随着这种生存方式的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同“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相反,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这两种利己主义者范畴和对现实人的现实关系的一种错觉上面的。个人利益的代表是“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这只是因为他必然与共同利益相对立,这种共同利益在现存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范围内以普遍利益的形式获得独立存在,从而在人们的观念中获得了理想利益的形式和意义。共同利益的代表是“自我牺牲者”,这只是由于他同以私人利益形式确定的个人利益相对立,只是由于共同利益被确立为普遍的和理想的利益。
“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和“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二者最终会合为自我舍弃。
第78页:“因此,自我舍弃是圣者和凡俗的人、纯洁的和不纯洁的人的共同特点:不纯洁的人舍弃一切善良的感情、羞耻甚至本性的畏怯,他只服从支配着他的那种欲望。纯洁的人舍弃自己和世界的自然关系……受金钱欲驱使的贪得者舍弃任何良心的劝告,舍弃一切荣誉感,他没有任何仁慈和同情心;他无所顾忌,他的欲望驱使着他。圣者的行为也是这样的:他使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笑柄,他‘冷酷无情’,他‘严守正义’,因为一种不可抑制的渴望控制了他。”
“贪得者”,这里是作为不纯洁的、凡俗的利己主义者,即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出现的,他只不过是儿童修身课本里司空见惯的、成为小说常见题材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破格的人物,而决不是自私自利的资产者代表,资产者相反用不着舍弃“良心的劝告”、“荣誉感”等等,也用不着自限于一个贪婪的欲望。相反,伴随着他们的贪欲一起来的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如政治的等等——欲望,资产者决不会牺牲对这些欲望的满足。这个问题我们不再深入探讨了,让我们立刻来谈谈施蒂纳的“自我舍弃”吧。圣麦克斯在这里用另一个只在圣麦克斯观念中存在的自我来代替舍弃自己的自我。他让“不纯洁的人”抛弃像“善良的感情”、“羞耻”、“畏怯”、“荣誉感”等等这些一般的特性,而他甚至连问都不问这个不纯洁的人是否具备过这些特性。好像“不纯洁的人”一定会具备这一切品质似的!但是,即使“不纯洁的人”具有这一切特性,抛弃这一切特性也并不意味着是自我舍弃,而只是说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甚至在“自我一致的”道德中得到辩解),那就是为了一个欲望而牺牲一些其他的欲望。最后,按照这种理论,“自我舍弃”既是桑乔所做的一切,也是桑乔所不做的一切。不管他是否愿意采取这种立场……[注:原稿至此中断,残缺地保留了以下这几段被删掉的话:“……他,利己主义者是自己本身的自我否定。在他追求某种利益的时候,他就否定对这种利益的漠不关心;在他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否定游手好闲。因此,对于作为‘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的桑乔来说,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向自己的‘绊脚石’证明,他经常否定自身,因为他经常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的对立面,而从不否定自己的真正的利益。
根据自我否定理论,桑乔可以嚷道(第80页):‘例如,难道无私是不真实的和任何地方也不存在的吗?相反,这是最平常的东西!’
德国小资产者意识的‘无私’真是使我们高兴……
他立即提出这种无私的好的例子,他指的是弗兰克的孤儿院,奥康奈尔、圣博尼法齐乌斯、罗伯斯比尔、克尔纳……
……至于奥康奈尔,这是英国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只有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才可以设想奥康奈尔是‘无私’的,——奥康奈尔,他为了供养自己的非婚生子女和扩大自己的财产而‘不倦地工作’;他不无道理地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律师的行业(每年一万镑)而改做更有利可图的鼓动家的行业(每年二万至三万镑),特别是因为在爱尔兰他没有对手;他当仲裁人,‘冷酷无情地”剥削爱尔兰的农民,迫使他们住在猪圈里,而他本人——这个唐恩国王——却在梅利安广场的宫殿拥有一所公爵庄院,同时又不断地为这些农民可怜的命运流泪,‘因为他被一种难以抑制的愿望所掌握’。他总是使运动达到足以保证他获得国赋以及领袖地位的限度为止,而每年征收赋税以后,他就丢开一切说教,在德利南那块自己的领地上养尊处优去了。奥康奈尔长期的法律欺骗行为和对他所参加的运动的极为无耻的从中牟利,甚至引起英国资产者的鄙视,尽管总的来说他对他们是极为有利的。
不过,很明显,对于圣麦克斯这个发现真正利己主义的人来说,证明世界上无私是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也口吐(“维干德”第165页)伟大的格言,说世界‘自古无私’。至多可以说,‘利己主义者’常常是作为施蒂纳的先驱而出现的,并‘推翻许多民族’。”——编者注]
虽然[注:页首有马克思的标记:“Ⅲ.意识”。——编者注]圣麦克斯在第420页里说:
“在我们的〔时代〕的门上写着的不是……‘认认自己!’而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这里我们这位教书匠又把他在经验中碰到的现实的价值的实现变成关于实现的道德诫条〉——
但是,那个“有名的阿波罗”[84]格言,应该是适用于“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而不适用于至此提到的“自我牺牲者”的,这句名言说: “你们要反复地认认自己,一定要了解你们的本来面目,并且丢开想成为不是你们而是另外一个什么的那种狂妄念头吧。”
“因为”: “这会造成受骗的利己主义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在满足自己,而只是在满足我的心愿中的一个,例如对幸福的渴望。你们的一切所做所为——不过是私自的隐蔽的……利己主义,无意识的利己主义,然而正因为如此,所以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做奴隶、当佣人、自我舍弃。你们是利己主义者,同时因为你们舍弃利己主义,又不是利己主义者。”(第217页)
“任何一头羊,任何一条狗也不会费心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利己主义者(第443页);“任何一个动物”也不会号召其他动物:你们要反复地认认自己,一定要了解你们的本来面目,——“要知道,你们的本性”是利己的,“你们”是利己的“本性,即”利己主义者。“但是正因为你们已经是如此了,你们就没有必要还再去成为这样的人物”(同上)。你们是什么,你们的意识也就属于什么。而且,因为你们是利己主义者,所以你们也就具有与你们的利己主义相符合的意识,就是说,你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追随施蒂纳的道德诫条,陷入自我探讨和忏悔。施蒂纳在这里又施展了哲学的旧花招,这种花招我们以后还要讲到。这位哲学家不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是人。他说:你们从来就是人,可是你们缺乏你们是人的意识,正因为如此,所以你们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人。所以你们的现象与你们的本质不符。你们是人又不是人。这位哲学家在这里转弯抹角地承认一定的意识也是有一定的人和一定的情况与之相符合的。但是同时他又认为:他向人们所提出的要他们改变自身意识的道德要求,会引起这种改变的自身意识,而在那些由于经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人们中(现在这种人所具备的当然是另一种意识了),他所看到的只是那改变了的[意识],此外再没有别的。[你们秘密地]追求的那个你们的[意识],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隐蔽的,不自觉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说,如果你们是不自觉的,那末你们真正是利己主义者;但如果你们是自觉的,你们就是非利己主义者。或者:你们现在的意识具有一个同我所要求的存在不相符合的一定的存在作为基础;你们的意识是一个本身不应该是的利己主义者的意识,从而它表明:你们本身是你们不应该是的利己主义者;换句话说,你们应该是一种与你们实际的样子不相同的人。意识同构成意识的基础的个人及其现实关系的完全割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者似乎没有与他的利己主义相符合的意识的这种幻想,——这些只不过是旧哲学的诡谲,而乡下佬雅各在这里却轻信地接受并加以模仿了[注: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这种奇怪的想法,如从历史方面来看,是最可笑不过的了。历史上晚期时代对早期时代的认识当然与后者对自己的认识不同,例如,古希腊人是作为古希腊人认识自己的,而不会像我们对他们的认识那样,如果指责古希腊人对自己没有像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认识,即‘对他们事实上是什么人这一点的认识’,就等于指责他们为什么是古希腊人。”——编者注]。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施蒂纳的贪得者的“动人例子”吧。这个贪得者不是一般的贪得者,而是贪得的“张三或李四”,是完全个别地确定出来的“唯一的”贪得者,并且他的贪欲不是“贪欲”的范畴(圣麦克斯从他的生活的复杂的、包罗万象的、“唯一的”表现中抽象出来的范畴),也“不取决于其他人〈如圣麦克斯〉怎样来标记这个贪欲”,圣麦克斯竟想对这个贪得者进行道德说教,向他证明他“所满足的并非自己,而是自己的一个欲望”。[然而“只在一瞬间,你是你,只是作为这一瞬间的你,你才真正存在。一种和你,和那一瞬间的人脱离开的”是某种绝对崇高的东西,如金钱。但是“对于你来说”,金钱“更确切些说”是最高的享受或不是,它对于你是某种“绝对崇高”的东西或不是……][注:下文严重损毁不清。——编者注]或者是在“舍弃”我自己吧?——他发现贪欲日夜占有着我;但食欲只在它的反思中占有着我。正是他把在其中我总是一瞬间的我、总是我本身、总是真实的我的无数时刻变为“日夜”,如同正是只有他用一个道德论断简括了我生命表现的各种方面,并且断言:这些方面是为满足贪欲而服务的。当圣麦克斯下判断说我所满足的只是我的一个欲望,而不是我自己,他这是把我作为一个充分完整的存在与我自身对立起来。“可是这个充分完整的存在是什么构成的呢?恰恰不是你的一瞬间的存在,不是你在这一瞬间是什么构成的”,按圣麦克斯自己的意思来说,因而是神圣的“本质”构成的(“维干德”第171页)。当“施蒂纳”说,我必须改变我的意识,可是在我这方面我知道我的一瞬间的意识也属于我的一瞬间的存在,而当圣麦克斯在争论这个意识之属于我的时候,他是在作为隐蔽的道德家干预我的整个生活道路[注:这里,在原稿页首马克思重新作了一个标记:“Ⅲ(意识)”。——编者注]。其次,“难道只有在你想到你自己时你才存在吗?难道只有依靠自我意识你才存在吗?”(“维干德”第157—158页)除了是利己主义者我还能是什么别的人呢?例如施蒂纳,不管他否认或者不否认利己主义,他除了是利己主义者还可能是什么别的人呢?你这样地说教:“你们是利己主义者,你们又不是利己主义者,因为你们抛弃利己主义。”
真是一位没有过错的、“受了骗的”、“不被赏识”的教书匠呀!但事情恰好相反。我们这些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我们这些资产者清楚地知道,charité bien ordonnée commence par soi-même〔良好地安排的慈善施舍从自己本身开始〕,而“爱人如己”这句格言我们早已解释成为每人都是自己的亲人。但我们否认我们是冷酷的利己主义者、剥削者、普通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的心肠是不能具备那种把他人的利益看作自己本人利益的崇高感情的。用你我之间的老实话来说,这只表示我们把自己的利益视为他人的利益而已。你否定唯一的利己主义者的“普通的”利己主义,只因为你“舍弃自己和世界的天然关系”。因此你不懂得,我们这些关心实现真正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不是利己主义的神圣利益的人,正是用抛弃利己主义空话的方法,来使实际的利己主义达到完善的地步。然而,也可以预见到(这里资产者无情地转过身去,背向圣麦克斯),你们这些德国教书匠们一旦来为利己主义作辩护,那你们所要宣告的不会是真正的、“世俗的、一目了然的”(“圣书”第455页)利己主义,就是说“已经不是那个叫作”利己主义“的东西”,而是非普通的、合乎学究理解的利己主义,哲学的或游民的利己主义了。
这样,非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现在才被发现”。“让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个新发现吧”(第13页)。
从上面所说可以看出,只要以前的利己主义者改变自己的意识,就能成为非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因此,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以前的利己主义者的差别只在于意识,也就是说,只在于他是具有知识的人,是哲学家。从圣麦克斯的整个历史观点,也可以看出另外一点,那就是因为以前的利己主义者都只被“圣物”统治着,所以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也就只要反对那“圣物”就行了。“唯一的”历史告诉我们,圣麦克斯把历史关系变为观念,然后把利己主义者变为违背这些观念的罪人,他把一切利己主义的自我实现变为违背这些观念的罪过,把例如特权者的权力变为违背平等观念的罪过,变为专制的罪过。因此,关于自由竞争观念,我们在“圣书”中可以读到(第155页):作者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的东西”……是属于伟大的……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的……是必要的而且是不能劫夺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战胜它们,那就是把它们变为神圣的东西,然后确信他来消除它们中的神圣性,即消除自己的关于它们的神圣观念,——而且,因为它们只在他这位圣者身上存在,从而也就把它们本身消除了[注:手稿的这个地方只是部分地保留了下来。——编者注]。
第50页[注:在这页手稿的开头马克思加了一个边注:“Ⅱ(创造者和创造物)”。——编者注]:“正如每一瞬间的你是什么样子,所以你,这个你自己的创造物也是什么样子,并且就在这个创造物中你不要把你这创造者失去了。你比之你自己是更高的存在,就是说,你不只是创造物,而且同样也是创造者,作为非自愿的利己主义者你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因此,这更高的存在对你即成为异己的。”
“圣书”第239页里用稍微不同的形式叙述了同样的高见: “类就是无〈类在以后却成为各式各样的东西,见“自我享乐”〉,如果个别的人凌驾于自己个性的局限性之上,那末正是在这里他自己才表现为单个的个人;只因为他总是上升,只因为他不停留于他现在的样子,这样他才存在,否则他就完了,成为死的了。”
施蒂纳立即以“创造者”的姿态来对待这些词句,对待他的“创造物”,并且“绝不在它们中失去自己”: “只在一瞬间,你才是你,只是作为这一瞬间的你,你才真正存在。在每一具体的时刻,我完整地是我而存在……一种和你,和那一瞬间的人脱离开的是某种”“绝对崇高”的东西……(“维干德”第170页);而在第171页上(同上)“你的存在”是作为“你的一瞬间的存在”加以肯定的。
虽然在“圣书”里圣麦克斯说,他在一瞬间的存在之外还具有另一个更高的存在,但在“辩护性的评注”里他的个人的“一瞬间的存在”却与他的“完整的存在”等同起来,每一个存在作为“一瞬间的”存在转变为“绝对崇高的存在”。因而,在“圣书”中在每一瞬间他是比他在这一瞬间更高的存在,而在“评注”中,一切他在这一瞬间不直接是的东西,就是“绝对崇高的存在”,就是神圣的存在。——在这整个二重化的情况之后,我们在“圣书”第200页中却看到: “关于‘不完善的’和‘完善的’我的二重化,我什么也不知道。”
现在“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已经不必为任何崇高的东西牺牲自己了,因为他对自己来说就是这种崇高的东西,“崇高的”和“低下的”这种二重化是他在自己身上带着的。这样,实际上(圣桑乔反对费尔巴哈,“圣书”第243页)“崇高的存在只不过是这里所经过的一种蜕变”。圣麦克斯的真正的利己主义就在于利己主义地对待实际的利己主义,对待“在每一具体的瞬间”是什么样的他自己本身。这种对待利己主义的利己主义态度就是自我牺牲。圣麦克斯从作为创造物这方面来说是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而作为创造者,他又是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我们也会认识到那对立的另一面,因为在完成那绝对辩证法的过程中(其中每一面就其本身说是它自己的对立面),它们两面作为真正的反思规定而互使对方合法化。在我们深入研究这奥秘及其各种隐蔽的形态以前,需要考察一下它在各次严重的生死博斗中的情形。
[施蒂纳在第82、83页中达到了从精神世界的观点看使这个作为创造者的利己主义者取得自我一致的最一般的品质。
“基督教的目的曾是使我们摆脱自然特性(由自然决定的特性),摆脱作为动力的欲望;因此,它曾力图使人不受自己欲望的支配。这并不是说他不应有欲望,只是说欲望不应统治他,不应该成为固定不变的、不可克制的和不能摆脱的。基督教用来对付欲望的这种手段我们能不能也用来对付基督教本身的教诫,说我们决定于精神呢?……这样一来,结果这就会使精神瓦解,使一切思想瓦解。正如那里必须那样说……那我们现在也可以说:诚然,我们应当掌握精神,但精神还应当掌握我们”。]
“凡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第5章第24节),看来,按照施蒂纳的意见,他们是作为真正的所有者带着钉在十字架上的邪情私欲而出现的。他承揽了基督教的传播,但不愿只满足于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而也想把精神、即“完整的主体”钉在十字架上。基督教之所以要使我们摆脱肉体的和“作为动力的欲望”的统治,只是因为它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看作某种与我们相异的东西;它之所以想要消除自然对我们的制约,只是因为它认为我们自己的自然不属于我们。既然事实上我自己不是自然,既然我的自然欲望,整个我的自然机体不属于我自己(基督教的学说就是如此),那末自然的任何制约,不管这种制约是我自己的自然机体所引起的还是所谓外界自然所造成的,都会使我觉得是一种外来的制约,使我觉得是枷锁,使我觉得是对我的强暴,是和精神的自律相异的他律。施蒂纳不加思考地接受了这种基督教的辩证法,然后又把它用来对待我们的精神。不过,基督教一直未能使我们摆脱欲望的控制,纵使从圣麦克斯偷偷地塞进基督教的那种狭隘的小市民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欲望的控制。基督教只限于空洞的、实际上毫无实效的道德说教。施蒂纳把道德说教看作实在的行动,并且用进一步的绝对命令加以补充说:“诚然,我们应当掌握精神,但精神不应当掌握我们”,因此:用黑格尔的话说,“只要进一步去考察”他的全部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都可以归结为既可笑又堂皇可观的道德哲学。
欲望是否成为固定,就是说它是否取得对我们的无上权力(不过这并不排斥进一步的发展),这决定于物质情况、“丑恶的”世俗生活条件是否许可正常地满足这种欲望,另一方面,是否许可发展全部的欲望。而这最后一点又决定于我们的生活条件是否容许全面的活动因而使我们一切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思想是否要变成固定的,也决定于现实关系的组成以及这些关系所给予每个个人发展的可能性,就如德国哲学家,这些quinousfontpitié〔使我们感到可怜的〕“社会牺牲品”的固定观念就同德国的条件有不可分的联系。此外,施蒂纳所说的欲望的控制是使他荣获至圣头衔的一句空话。我们还是回到贪得者这个“动人的例子”,我们读到:
“贪得者不是所有者,而是奴隶,如果他不同时秉承他的主人的意志做事,凭他自己,他就什么也不能做。”(第400页)
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这对施蒂纳来说,就意味着这需要和它的器官就成为他的主人,正如以前他曾把满足需要的手段(参看“政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节)作为自己的主人一样。施蒂纳若不是同时为了胃而吃饭,是不可能吃饭的,如果世俗生活关系妨碍他满足自己的胃,那末他的胃就成为他的主人,吃饭的欲望就成为固定的欲望,而吃饭的想法就成为固定观念,这一切又给他提供了一个例子来证明世俗生活条件对他的欲望和观念固定化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桑乔反对欲望和思想的固定化的“暴动”,可说是关于自我控制的无力的道德说教,并再一次证明他不过是赋予小资产者的最庸俗的念头以思想上夸张的说法[注: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由于共产主义者攻击那一直在引起愿望或思想必然僵化的物质基础,因此他们才是唯一能够依靠自己的历史作用,使正在僵化的愿望和思想的重新融化得以真正地实现,而不再是‘截至’施蒂纳为止的一切伦理学者所做的无力的道德说教。共产主义组织对当前的关系在个人中引起的愿望有两方面的作用;这些愿望的一部分,即那些在一切关系中都存在、只是因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在形式和方向上有所改变的愿望,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也会改变,只要供给它们正常发展的资料;另一部分,即那些只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一定的生产和交往的条件下的愿望,却完全丧失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肯定哪些欲望在共产主义组织中只发生变化,哪些要消灭,——只能根据实践的道路、根据真实欲望的改变,而不是依据与以往历史关系的比较来决定。我们刚才为了在这‘唯一的’事实上粉碎施蒂纳而用的‘僵硬的’和‘愿望’这两个词汇,当然是完全不恰当的。有这样一个事实:现社会中个人的一种要求可以靠牺牲其他一切要求来满足以及存在着一种道德的条件,既这种情况‘不该产生’,然而现世界的一切人的情况却plusoumoins〔或多或少地〕正是如此,因此使一个完整的人不能自由发展,——对于这一事实和现存社会制度的经验联系一无所知的施蒂纳把这一事实说成是非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愿望在僵化’。愿望只要是一种存在,它就是某种‘僵硬’的东西,只有圣麦克斯和他的伙伴才想得出不使自己的例如性欲变成‘僵硬的’,然而这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只有阉割或阳萎的结果才不再如此。作为某种‘愿望’的基础的任何一种需要,也都是某种‘僵硬的’东西,而圣麦克斯怎样努力也不能消除这种‘僵硬性’,也不能做到例如这样的事,即可以经过许多‘僵硬的’时候不必吃饭。共产主义者就没有想过要消灭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的这种僵硬性,这是施蒂纳在幻想时强加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一切人的身上的;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只是这样一种生产和交往的组织,那里他们可以实现正常的,也就是仅限于需要本身的一切需要的满足。”——编者注]。
在这第一个例子中,当他的创造物想要脱离他即它们的创造者而自求独立时,他因而一面与自己肉体的欲望斗争,一面与自己的精神思想斗争;一面与自己的肉体斗争,一面与自己的精神斗争。至于我们的圣者怎样进行这一斗争,他作为创造者对于自己的创造物的态度如何,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在“通常理解的”基督教徒那里,用傅立叶的说法,在chrétien《sim-ple》〔“简单的”基督教徒〕那里,“精神握有完全的统治权力,它对‘肉体’的任何异议都置之不理。但是,我只能用‘肉体’摧毁精神的专制,因为一个人,只有当他同样理解了自己肉体的意愿时,才能完全理解自己,只有完全理解了自己,他才成为一个有理解力、有理智的人……然而,只要肉体一发言,那它的声调就是狂热的声调——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这位cjrétien simple〉就觉得似乎听到了魔鬼的声音,反对精神的声音……他只得奋起抵抗它们。假使他容忍它们,那他就不是基督教徒了。”(第83页)
于是,当圣麦克斯的精神想要脱离他而自求独立时,他就号召自己的肉体来支援;当他的肉体反叛起来时,他又想到原来他也是精神。基督教徒在一面做的事,他同时在两面进行。他是chrétien《composé》〔“复杂的”基督教徒〕,他再一次表明自己是完善的基督教徒。这里的这个例子中,作为精神的圣麦克斯并不表现为自己肉体的创造者,反过来,也不作为肉体表现为精神的创造者。他拥有现成的肉体和精神,只有当二者之一起来暴动时,他就想到,他还有另一面,于是把这一面当作自己的真实的我提出来反对前者。因此,圣麦克斯在这里是创造者,这只不过是因为他“还具有另一种性质”,这是因为除了现在他乐于归之为“创造物”范畴的东西以外,他还具有另一种特质。理解自己并且理解自己的整体,或成为有理智的人[注:因此,圣麦克斯在这里完全证实了费尔巴哈关于妓女和情人的“动人的例子”。一个人在前者那里“领会”的只是自己的肉体的声音,或只是她的肉体的声音,而在后者那里他领会的是自己的整体,或她的整体。见“维干德”第170、171页。],了解自己是“完整的存在”,是和“他的一瞬间的存在”不同,甚至和他在这个具体“瞬间”是什么样的存在正相反的存在,这种良好的意图就是他在这里的全部创造活动。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位圣者的一次“严重的生死搏斗”:
第80、81页:“我的热情可能不次于最狂热的东西,但同时我对待它却冷酷无情、毫不信任,像是它的死敌一样;我是它的主宰,因为我是它的所有者。”
如果圣桑乔关于自己的这些言论有意义的话],那末他这里的创造活动就限于:他在自己的热情中保有对这种热情的意识,他对它进行反思,他是作为进行思考的我来对待作为现实的我的。意识——这就是他随意加上“创造者”头衔的东西。他之所以是“创造者”,只不过因为他拥有意识。 “就此,你在甜蜜的自我遗忘中忘记了你自己……但是,难道只有在你想到你自己时你才存在,而在你忘记你自己时你就消失了吗?哪一个人不是每一瞬间都在忘记自己,哪一个人不是在一小时中倒有一千次忘记了自己呢?”(“维干德”第157、158页)
当然,桑乔不能为了他的“自我遗忘”而忘记这一点,因此他“同时像是它的死敌一样”来“对待”它。作为创造物的圣麦克斯燃烧起不平常的热情的火焰,就在同时,作为创造者的圣麦克斯却借助于反思而凌驾于这种热情之上;或者:现实的圣麦克斯满腔热情,而反思着的圣麦克斯却觉得自己是凌驾于这种热情之上。这种在反思中凌驾于现实的他之上的情况是用引人入胜的美文学的笔法来描绘的,这样就能使他继续保持他的热情;也就是说,使他对这种热情的仇视不认真地去对待,而是“冷酷无情”地、“毫不信任”地、像“死敌”一般地对待它。圣麦克斯当其满腔热情,也就是说当热情是他的实在的特性,那他不是作为创造者来对待它的;而当他作为创造者对待其热情时,他就不是具有真正的热情,热情对他说来成为异己的东西,不是他所固有的了。只要他满腔热情,他就不是热情的所有者,而一旦他变成它的所有者时,他就不再是满腔热情的了。他是一个完整的综合体,在每一瞬间他是他的一切特性的总和的创造者与所有者,这里只须除去其中一个特性,那就是用来作为创造物和所有物同作为其余一切特性的总和的我对立起来的特性,因而恰恰是他所强调是他自己的特性的那个特性,总是成为对他说来是异己的东西。
不管圣麦克斯在自己本身中、在他本身的意识中所玩弄的英雄业绩的真实历史听来如何玄妙,但是总有一个无人不晓的事实,那就是:恰恰正是有一些反思的人,他们相信在反思中并借助反思之力,能够超越一切[注: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实际上这一切只是资产者所唱的高调。他经常掌握自己心灵的每一活动,以免遭受损失,同时却夸耀自己的各种特性,例如博爱的热情,而为了使自己不失为所有者,继续作为博爱的所有者,他对于博爱本应‘冷酷无情、毫不信任和充满最坚决的敌意’。然而圣麦克斯为了自己的反思的我、为了自己的反思,却牺牲了他应该像对‘死敌’那样对待的特性,而资产者牺牲自己的欲望和愿望时,总是为了一定的实际的利益”——编者注],然而实际上他们却从未能从反思中超脱出来。
作为具有其他特性的人,在这个例子里作为对付对立物的具有反思的人,来反对某个确定的特性,这种手法只要加以必要的变更是可以用于随便什么特性的。例如,我的无所谓的态度可能不次于玩腻了的人的无所谓的态度;然而我同时却可以激昂慷慨地、绝不相信地,像死敌一样地反对这个无所谓的态度。
[不要忘记,他的一切特性的那个完整的综合体,即圣桑乔在反思中作为与一个确定的特性对立的所有者,在这里不是别的,这就是桑乔对这一特性的简单反思。他把这特性变成他的我,他所提出的不是完整的综合体,而单就是一个纯反思的特质,以与每一个特性以及全部特性的总和对立的,就仅仅是这个反思的特质,某个我],自己想像的我。
这种对自己本身的敌视态度,这种对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特性的边沁式簿记的夸张讽刺[85],现在由他自己讲出来了。
第188页:“某种利益,不论它指向什么,如果我不能摆脱它,它就会使我成为它的奴隶;那它就不是我的所有物,而我却是它的所有物了。让我们接受批判的指示吧!让我们在摆脱中感到自由自在吧!”
“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可是“我们”想也没有想到过“接受批判的指示”。这样,此刻正处于“批判”的警察监视之下的圣麦克斯在这里要求“所有的人都感到同样的幸福”、“所有的人在同一环境中都感到同样的幸福”,“直接受宗教的暴虐统治”。他的非通常理解的对利害的关心在这里表现为天上的对利害的漠不关心。
不过,在这里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谈,在现存社会中“某种利益是否要使他成为它的奴隶”以及“他能否摆脱它”,根本不决定于圣桑乔。由于分工和阶级关系而产生的利益的固定化远比“欲望”和“思想”的固定化明显得多。
为了胜过批判的批判,我们这位圣者至少需要达到摆脱的摆脱,因为否则摆脱就会成为他摆脱不掉的、使他成为奴隶的一种利益。摆脱已经不再为他的所有物,而他为摆脱的所有物了。[假如他想在刚刚所举的例子中贯彻始终,那末他必须把反对自己的“热情”的自己热情作为一种“利益”来对待,从而自己再“像死敌一样”来对待它。但是他也要注意他对“冷酷的”热情的那种“冷酷的”漠不关心,同样他也要成为完全“冷酷无情的”人,这样他自然会使他最初的“利益”,从而也使他自己,避免了在思辨中转圈子的“诱惑”],他不这样做,却满不在乎地继续写道(同上):
“我所关心的仅仅是对我保证我的所有物〈即在我的所有物之前保证我自己〉,并且,为了保证它,我每时每刻都把它回收到我自身之内,消灭它的哪怕一点点的突发的独立性,并且在它还没有来得及固定起来而成为固定观念或癖好之前就把它吞咽下去。”
看!施蒂纳竟然把属于他所有的人们怎样去“吞咽”吧!施蒂纳刚才让“批判”给他强加上某种“使命”。他声言,他立刻就又把这个“使命”吞咽了,在第189页中他说道:
“但是,我这样做并非为了我的人类使命,而是因为我召唤我自己去做的”。
当我不召唤我自己去这样做时,正如我们刚刚听到的,我就是奴隶,不是所有者,不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我就不是像我作为真正的利己主义者所应做的那样,作为创造者来对待自己;可见,只要有人想成为真正的利己主义者,那他就应该号召自己去履行“批判”所指示给他的这种使命。因此,这是普遍的使命,是一切人的使命,不仅是他的使命,而且也是他的使命。另一方面,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表现为大多数个人所不能达到的理想,因为(第434页)“天生的笨人无疑地是为数最多的一类人”,但这些“笨人”如何能洞察无限制的自我和整个世界的吞咽的奥秘呢。其实,这一切可怕的字眼,如消灭、吞咽等等,只不过是上述的“死敌的冷酷无情”的新说法而已。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看透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反对了。这些反对意见不过是他那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的预先的、隐蔽的合法化,在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之中,这些反对意见的真身复活了。[“所有的人在同一环境中都感到同样的幸福”复活为一种要求,要“我们在摆脱中感到自由自在”。“操心”复活为对自己保证把自己的我作为所有物那种唯一的“操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产生一种“操心,即如何”达到统一,达到创造者和创造物的统一。最后又出现了人道主义,它表现为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作为不能达到的理想出现在经验的个人的面前。]因此,“圣书”第117页上的话应该读作: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力图真正地把每个人都变成“秘密警察国家”。“反思”这个密探、这条警犬跟踪着精神和肉体的每一动作,对它来说一切行动与思想以及生命的每一表现都是反思的事情,即警察的事情。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就包含在人的这种肢解,人的这种分为“天生的欲望”和“反思”(我们身体内部的暴民、创造物和内部的警察、创造者)的分裂之中[注: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不过,如果有‘一个普鲁士的高级军官’对圣麦克斯说道:‘每一个普鲁士人心中都要提防自己的宪兵’,那末,很明显,圣麦克斯会说:提防国王的宪兵;只有‘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才提防自己本身的宪兵。”——编者注]。
赫斯(“晚近的哲学家”第26页)这样责备我们的圣者:
“他经常处于自己的批判良心的秘密警察监视之下……他没有忘记“仅仅在摆脱中感到自由自在……这个批判的指示’……他的批判良心总在提醒他:利己主义者对任何东西不应该感兴趣到完全醉心于自己的对象的地步”云云。
圣麦克斯“授权自己”对这一点这样反驳道: “赫斯讲到施蒂纳,说他似乎经常处于……等等,这不过表示施蒂纳在批判时,不愿随便批判〈这里顺便解释:这就是说,不用唯一的方式来批判〉,不说废话,而是真正地〈即像人一般地〉批判。”
至于赫斯讲到秘密警察等等,这还“表示着什么”,从上面举出的赫斯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圣麦克斯对这些话的哪怕就是他的“唯一的”理解也只能解释为故作不解。他的“思维的绝技”在这里变成欺骗的绝技,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而责难他,因为这种绝技在这里也是他的唯一的出路,但是,这和他在“圣书”中另一处所引用的有关撒谎的权利问题的精细入微的分析却很不相称。其实,“他在批判时”完全不是什么“真正地批判”,而是在“随便批判”和“说废话”,这我们已经用了比值得做的更多的篇幅向桑乔证明过了。所以,作为创造者的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对于作为创造物的自己的关系,首先是这样确定的:他肯定自己是具有其他特性的存在物,是肉体,以与肯定自己为创造物的那种确定性,以与例如自己作为有思维的、作为精神的自己相对立。随后他又不再主张自己是真正还具有其他特性的存在物,而只是一般地还有其他特性存在的一个简单观念,也就是说,在上述的例子里,作为也不思维的、没有思想的、或对思维漠不关心的存在物,然而当他发现这个观念是荒谬的时候,他又把它抛弃了。请参看前面所讲在思辨中转圈子的地方。所以,这里创造性活动就在于,反思这样的一种规定(这里指思维)对他也可能是无关痛痒的,也就是说创造性活动就在于一般地进行反思;结果,假如说他创造了什么东西的话(例如对立的观念,它的显而易见的实质却五花八门变幻莫测地被掩饰起来了),那末他所创造的当然也只是反思中的规定。
至于他作为创造物的内容,那末我们已经看到,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创造这个内容,也没有创造这些确定的特性,例如他的思维、他的热情等等,而是仅仅提供了作为创造物的这个内容在反思中的规定,仅仅提供一种这些确定的特性是他的创造物的观念。他的一切特性早就是他所特有的,至于它们是从哪里产生的,却与他无关。就是说,无须他来形成这些特性,例如学习跳舞,以便成为自己双足的主人,或者就非任何人都有、非任何人都能求得的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思想,以便成为自己思维的所有者;也无须他操心社会关系问题,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实际上施蒂纳只是靠一种特性摆脱另一种特性(即用这“另一种”特性摆脱自己的其他特性的压抑)。但是,我们已经指出,事实上他之所以能摆脱这种特性,只是因为不仅这个特性达到了自由发展和不再是单纯的天赋,而且也因为正是由于分工的结果,[社会关系允许他均匀地发展全部的特性,因为社会关系因此允许他主要地实现一个唯一的欲望,例如著书的欲望。像圣麦克斯那样,设想可以脱离一切其他欲望来满足一个欲望],可以不同时满足自己这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个人而满足这一个欲望,[这种设想完全是荒谬的。]如果这一个欲望取得抽象的、独立的性质,如果它成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同我对立起来,如果因此个人的满足就表现为片面地满足一个唯一的欲望,那末,决不像圣麦克斯所想的那样决定于意识或“善良意志”,更不是决定于对特性这一概念反思得不够。
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助。并且这个受到特别培植的特性发展的方式如何,又是一方面决定于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决定于其他特性被压抑的程度和性质。正因为思维(以思维为例)是这一确定的个人的思维,所以这个思维就是他的由他的个性和他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关系所决定的思维;就是说,有思维的个人完全没有必要对思维本身进行长时间的反思,才来宣告自己的思维是自己的思维,是自己的所有物,因为它从开头就是他所有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思维,而且正是他的这个独特性[被圣桑乔视为这一特性的“对立面”,视为只在“自身”中存在的独特性]。例如一个人,他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因此是过着一个多方面的生活,这样一个人的思维也像他的生活的任何其他表现一样具有全面的性质。因此,当这个人从思维转向某种其他的生活表现时,他的思维并不会僵化为抽象的思维,也不需要在反思上耍什么复杂的花样。它从开头就是按照需要时而消灭时而出现的个人整个生活中的一个因素。
而局限于地方范围的柏林教书匠或著作家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活动仅仅是一方面辛苦工作,一方面享受思维的陶醉,他们的世界就限于从莫阿毕特区到科比尼克区,钉死在汉堡门以内[86],他们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同世界的关系降至最低限度。在这样的人那里,当他具有思考的需要时,他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一样地抽象,而且对于这个毫无抵抗的人成为一种惰性力量,这种惰性力量的活动使他有可能从他的“丑恶的世界”中获得片刻的解脱,使他能得到瞬间的享乐。在这样的人那里,那些余下不多的与其说由于和外界交往而产生的、不如说由于人的身体结构而产生的欲望,只是以反射的推动力来表现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局限的发展范围内采取同思维同样片面而粗暴的性质,它们经过长时间的间隔在畸形发展的统治欲望的刺激下(受直接的肉体原因的支持,[例如胃痛)出现,猛烈地、强横地表现出来,粗暴地排斥一般的正常的欲望,这样用来进一步加强它们对思维的控制。自然,教书匠的思想在对这种经验的事实进行思考时也是按照教书匠的方式而反思和琢磨的。但只是简单地宣告施蒂纳是一般地“创造”了自己的特性,这连它们向某一特定方面的发展也解释不了]。这些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这并不决定于施蒂纳,而是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这绝对不是因为人们在反思中想像他们似乎消灭了或者在想像中决定要消灭自己的地方局限性,而只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经验的实际中以及由于经验的要求造成了世界交往[注: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圣麦克斯在最后一个世俗的地方承认:我从世界那里获得(费希特的)‘推动力’;共产主义者故意把这种‘推动力’加以控制,诚然,这种‘推动力’(如果不是限于空洞的词句)变成了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推动力’,当然,这对于圣麦克斯说来是过于大胆的思想,他是不可能谈到这种思想的。”——编者注]的这一事实,使个别的人在顺利的条件下可能超脱地方局限性。
我们这位圣者通过对自己的特性和欲望的痛苦的反思所达到的唯一的结果就是,由于他不断地同自己的特性和欲望纠缠刁难,因而使自己对它们的享受和满足大大地打了折扣。
上面已经讲过,圣麦克斯所创造的只是自己这个创造物,就是说,他只限于把自己归结为创造物这个范畴。[他作为创造者的活动就在于把自己看作是创造物,并且他甚至不想重新消灭这个作为他的产物的把自己割裂为创造者和创造物的这种二重化。二重化为“本质的”和“非本质的”,这成为他的永恒的生命过程,因而也就成为简单的假象,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连一个实际的存在都不是,而且因为它只存在于“纯粹的”反思中,由于存在总是在他和他的反思之外,所以他的力图把反思想像成为某种实体的东西,也成为徒劳。
“然而,既然这个敌人〈即作为创造物的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在自己的失败中创造自己,既然意识集中在他身上,不离开他,而是经常停留在他身上,并且总是认为自己受了玷污,既然他的努力的这个内容同时又是最低贱的,那末我们看到的就只能是一个局限于自身和自己的琐事的〈即无所作为〉忐忑不安的、又不幸又可怜的个人。”(黑格尔)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讲的有关桑乔二重化为创造者和创造物的这一点,他终于以如下的逻辑形式表达出来:创造者和创造物转变为假设的我和被假设的我,从而(就[他对他的我所作的]假设是一种设定而言)变为设定的我和被设定的我: “从我这方面来讲,我是以某种假设为出发点的,因为我以我为假设;但我的假设并不力求完善〈恰当些说,圣麦克斯力求把它贬低〉,而只是作为我的享乐和吞噬的对象〈好令人羡慕的享乐!〉。我只靠我的假设吃饭,我只是因为吞噬它才生存。因此〈好一个“因此”!〉这个假设完全不是假设;因为〈好一个“因为”!〉我是唯一者〈应读为:真正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我全然不晓得假设的我和被假设的我(“不完善的”和“完善的”我或人)的二重性〈应读为:我的我之完善性只是由于知道我在每一瞬间是不完善的我,是创造物〉,但是〈伟人的一个“但是”!〉我吞噬自己,这只表示我存在着〈应读为:我存在着的这个事实,在这里只意味着我在想像中吞噬了我所固有的被假设者的范畴〉。我不假设我自己的存在,因为我还只不过在每一瞬间在设定或创造我自己〈即设定或创造其作为被假设者、被设定者或被创造者〉,并且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不是被假设的,而是被设定的〈应读为:并且我之所以存在着,只是因为在我的设定之前我就被假设了〉,而我之被设定又只是在我设定我自己的那一瞬间,也就是说我一身既是创造者又是创造物。”
施蒂纳是“肯定的成人”,因为他总是被设定的我,而他的我“又是成人”(“维干德”第183页)。“因此”,他是肯定的成人;“因为”他的欲望从未驱使他做出过火的行为,“所以”他就是小市民所说的肯定的成人,“然而”他是肯定的成人这一事实,“只意味着”他对自己本身的转变和变形总是一笔笔账记得很清楚的。到现在为止(依施蒂纳如法泡制,我们也来一次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只是“自为的”东西,即除了一般的反思特性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创造活动,现在由施蒂纳本人加以“设定”了。圣麦克斯对“本质”的斗争正是到这里达到了他的“最终目的”,他把自己本身跟本质甚至跟纯粹思辨的存在等同起来。[创造者和创造物的关系变成对自我假设的解说,也就是说,施蒂纳把黑格尔在“本质论”中关于反思所说的一切变成极端“无力”而混乱的观念。事实上,由于圣麦克斯所抽出的是自己反思的一瞬间,即在设定着什么的反思,因此他的幻想就成了“否定的”:他为了把自己作为设定者和被设定者区分开来,把自己等等都变成“自我假设”,也把反思变成创造者和创造物的神秘的对立。]顺便指出,在“逻辑学”的这一节中黑格尔分析“创造性的无”的各种“花招”,这说明了为什么圣麦克斯早在第8页上就已经把自己“设定”为这个“创造性的无”。
现在我们“插曲般地插入”黑格尔说明自我假设的某几段,以便与圣麦克斯的解说对照一下。但是,由于黑格尔不像乡下佬雅各那样写得前后不连贯,那样“随便”,我们就不得不从“逻辑学”一书的不同各页中搜集几段,以便与桑乔的伟大语句相吻合。
“本质以自身为前提,而这个前提的扬弃就是它自身。既然它是自身对自身的排斥,或者是对自身的漠不关心,是对自身的否定态度,因此,它把自己和自己对立起来……设定是没有前提的……他物仅仅是由本质自身假设的……因此反思仅仅是对自身的否定。作为提出假设的反思来说,它仅仅是设定的反思。因而它是自身和非自身的一个统一体。”〈“创造者和创造物的统一”〉(黑格尔“逻辑学”第2册第5、16、17、18、22页)
在施蒂纳的“思维的绝技”之前应该可以期待,他会去进一步探求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他明智地没有这样做。否则他会发现他作为仅仅“被设定的”我,作为创造物,也就是说,就他拥有现有存在来说,只是假象的我,至于说他是“本质”,是创造者,那只是由于他不存在,而仅仅是想像着自己。我们已经看到,而且还会看到,他的一切特性,他的一切活动和他整个对世界的态度是他为自己制造的一个空洞假象,是“在客观事物的绳索上耍杂技”。他的我永远是哑巴的我、隐蔽起来的“我”,这个我隐蔽在他的那个被想像为本质的我之中。既然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在他的创造活动中仅仅是思辨的反思或纯本质的一种解释,因而“就像神话中所载的”,“通过自然的繁殖”就形成了我们在观察真正利己主义者的“严重的生死搏斗”时所已经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创造物”只是一些最简单的反思规定,[例如:同一、差别、平等、不平等、对立等等。这些反思规定,他企图根据他的“我”(“这个‘我’是远近皆知的”)来为自己加以说明,关于他的那个没有前提的我,我们偶尔还会“听到一些”],请参看“唯一者”。
在桑乔的历史虚构中,按照黑格尔的方法,最近的历史现象变成了原因,变成了较早的历史现象的创造者,同样,在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那里,今天的施蒂纳变为昨天的施蒂纳的创造者,虽则用他的话来说,今天的施蒂纳乃是昨天的施蒂纳的创造物。但是反思却把这一切颠倒过来,在反思中作为反思的产物、作为观念,昨天的施蒂纳成为今天的施蒂纳的创造物。同样,在施蒂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
第216页:“不要在‘自我舍弃’中寻求那个恰好把你同自身分离的自由,而要寻求自身〈即在“自我舍弃”中寻求自身〉,要成为利己主义者,但愿你们每个人都成为万能的我!”
在看到上述论题之后,我们就不会惊奇,后来圣麦克斯又以创造者和死敌的姿态来对待这句话,并且把他的“每个人都成为万能的我”这个崇高的道德主张“归结为”每个人本来就做他所能做的事,而他能做的事也正是他所做的事,因而每个人对圣麦克斯来说当然都是“万能的”。此外,在上面引用的那句话中集中地结合了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全部荒谬。首先是探求而且是自身的探求的道德训条。接着是把这探求作如下的规定:人应当成为他还不曾是的某种东西,即利己主义者,而这个利己主义者被确定为“万能的我”,在这里特殊的威力从真实的威力中转变为我,转变为万能,转变为威力的幻想。因此,探求自身,也就是要成为和现在的你不同的另一个你,而且成为万能的,那也就是说,成为空无所有,四不像,幻影。现在我们已经前进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能够揭穿唯一者的最深奥的秘密之一,同时也能解决长期使文明世界惶惶不安的一个问题。
施里加是什么人?从批判的“文学报”出版时起(参看“神圣家族”),凡是注意德国哲学发展的人都这样询问。施里加是什么人?大家都在询问,都在警觉地倾听这个名字的野蛮声音,但是没有回答。
施里加是什么人?圣麦克斯给了我们一把开启这个“一切秘密的秘密”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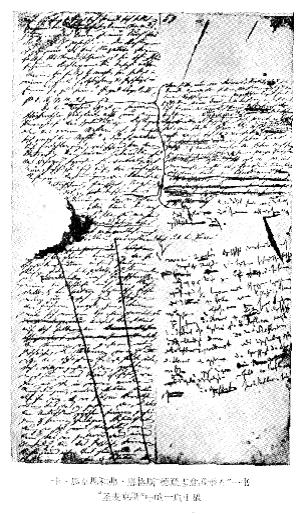
施里加,这是作为创造物的施蒂纳;施蒂纳,这是作为创造者的施里加。施蒂纳是“圣书”中的“我”,施里加是“圣书”中的“你”。因此创造者施蒂纳把自己的创造物施里加当作自己的“死敌”。一旦施里加想脱离施蒂纳而独立,——他在“北德意志杂志”中曾为此作过倒霉的尝试,——圣麦克斯就把他“吸入自身”;这种为反对施里加的企图而作的试验,是在“维干德”上所载的“辩护性的评注”第176—179页上进行的。但是创造者对创造物的斗争,即施蒂纳对施里加的斗争,只不过是表面的斗争:[现在施里加举出他的创造者本人的话例如“躯体本身,躯体自身就是无思想”(“维干德”第148页)来反对他的创造者。正如我们看到的,圣麦克斯在这里想的是纯粹的肉体,是形成之前的躯体,并把躯体确定为“与思想不同的他物”,确定为非思想和非思维],即无思想;后来他在一个地方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只是无思想(这等于过去只是肉体一样——因此,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才把他从思想中解救出来(第196页)。——我们在“维干德”那里发现还有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例证来证明这种神秘的联系。我们在“圣书”第7页上已经看到,“我”、即施蒂纳,是“唯一者”。在“评注”第153页上他对他的“你”说:“你”……是“词句的内容”,即“唯一者”的内容,而在同一页上又写着:“他本人,施累加,是词句的内容,这一点他却忽略了。”“唯一者”就是词句,正如圣麦克斯一字不差地所说的那样。作为“我”,即作为创造者来说,他是词句的所有者;这就是圣麦克斯。作为“你”,即作为创造物来说,他是词句的内容;正如刚才所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施里加。作为创造物的施里加以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以完全倒了霉的堂吉诃德的姿态出现;作为创造者的施蒂纳以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以圣桑乔·潘萨的姿态出现。
因此,在这里出现了创造者和创造物之间的对立的另一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都包含着自身的对立。桑乔·潘萨—施蒂纳,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通过自己关于圣物统治世界的信念战胜了堂吉诃德—施里加,自我牺牲的和空想的利己主义者,战胜了恰好作为堂吉诃德的他。[施蒂纳的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不是桑乔·潘萨,那又是什么呢,他的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不是堂吉诃德,那又是什么呢,而在他们迄今的形式下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是桑乔·潘萨—施蒂纳同堂吉诃德—施里加的关系,那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现在作为桑乔·潘萨的施蒂纳之所以把自己当作桑乔,只是为了使作为堂吉诃德的施里加相信,他在堂吉诃德精神方面胜过了他,而为了适应这个角色,即作为那种普遍的堂吉诃德精神的代表,施蒂纳丝毫也不会反对以前是他主人的堂吉诃德精神(即他以仆人的最大忠诚所效忠的堂吉诃德精神)],从而也在这里表现了塞万提斯已经描述过的狡猾。因此,按照他的真正内容来说,他是讲求实利的小资产者的维护者,但他却奋起反对与小资产者相适合的意识,这种意识归根到底是小资产者对于他们所高攀不上的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观念。
可见,堂吉诃德现在通过施里加而为他的先前的侍从效劳。
桑乔在每一页上都表明,他在何等程度上还在自己的新“转变”中保持着自己的旧习惯。“吞咽”和“吞吃”仍然是他的主要特性,“天生的怯懦”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着他,以至于普鲁士国王和亨利七十二世公爵,在他眼里都变成了“中国皇帝”或者“苏丹”,因此,他只打算谈谈“德……[注:德国的。——编者注]议院”;他仍然把自己口袋中的陈词滥调撒满在自己的周围,仍然害怕“怪影”,甚至断言,怪影是唯一可怕的东西;唯一的区别在于,当桑乔还没有成为圣者之前,他被下等客店中的粗人欺哄,而当他成为圣者时,他不断地欺哄自己。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谈施里加。谁不早就在圣桑乔借“你”的口说出的“词句”中发现有施里加的指点呢?不仅在这个“你”的词句中,而且在那些关于施里加以创造者的姿态、即以施蒂纳的姿态出现的词句中,也总能够发现施里加的踪迹。但是,既然施里加是创造物,所以在“神圣家族”中他只能是作为一个“秘密”出场。揭穿这个秘密落在创造者施蒂纳的身上。的确,我们模糊地感觉到,这里发生着某种伟大的、神圣的事件。我们总算没有被骗。唯一的事件真正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它甚至超过了塞万提斯在第20章中所描写的风车之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