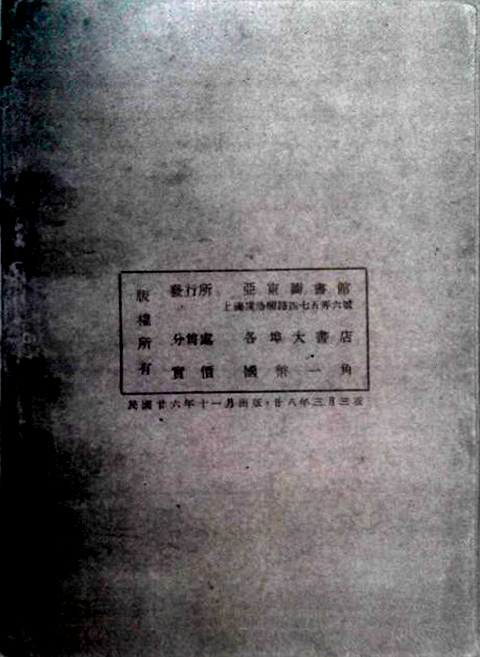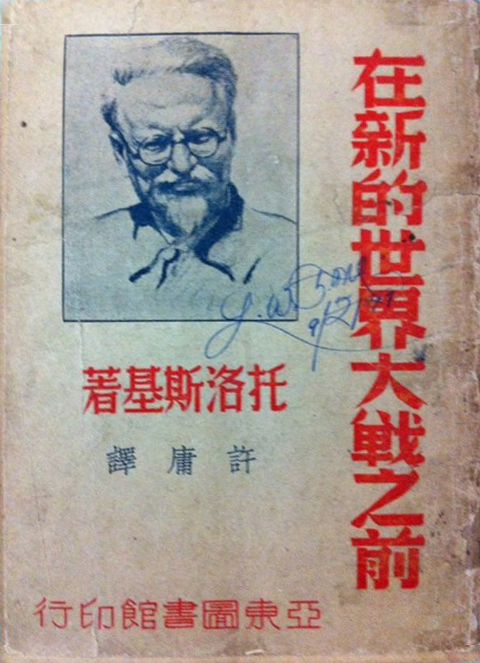
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
(1937年8月9日)
译者:許庸(王凡西)
译者序
近年来为人们当作谈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已到了爆发的前夜了。现在这大战不再是理论的预测,或渺茫的远景,而是迫切的威胁,且与全世界人士的生命福利有着最直接关系的事件了。
处在这一大灾难的前夜,有的人在悲惨地哭泣,有些人却仿佛看到新的希望,脸现微笑;再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们,如法西斯党徒,帝国主义者,军火商,军事家等,则以为时机来临,正在露齿狞笑;可是我们既不必哭,更毋须笑,我们的任务只在用清晰的头脑去求得理解。
人类为什么非进行这最残酷的战争不可?将来的战争到底要以何种方式爆发?何时爆发?两方的阵线如何?战争的可能结果如何?以及怎样才能有效地消灭战争?这一切问题,恐怕占领着每一个人的头脑吧?
这本小册子就是要帮助人们去理解这些问题的。
关于本书的作者,我们已毋须加以介绍,他那一生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当今第一流的革命家,政治家而兼军事家。具有这样资格的人来写这本论战争的书,那末他见解的高超与精深,固不用我这浅陋者再来多事唠叨的了。
译者。一九三八年。
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
“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斯宾诺莎
国际集团的不确定性
每天的报纸都在向世界的地平线上瞭望着,寻觅烽烟。要列举战争可能发生的地方,须有一本完善的地理教本的帮助。同时,国际的对抗如此的复杂和混乱,不但是战争在什么地方爆发,而且战争双方的同盟者是哪些国家,谁也不能精确的预言。射击是一定的,但谁对谁可不知道。
在一九一四年主要的不确定的因素是英国,她在没有帮助欧洲互相残杀之前,所关心的是维持欧洲的均势。第二个不确定的因素是意大利,她和德国、奥、匈的同盟有三十五年的历史,在大战的时候,她却掉转枪头反对同盟者。强大辽远的美国,也是一个谜,她只在大战的最后的决定的阶段,才加入战争。小国更增加了计算中的不可知的因素。然而在当时环境中,最稳定的因素,开始就是德奥与法俄的同盟。这两个同盟就决定了军事行动的轴心,其余的参加者需要围绕于这轴心的周围。
昔日的两个阵营之对峙的相对的稳定性,现在是谈也不要谈了。伦敦的政策决定于英帝国在世界各部分的利益的矛盾,现在这政策比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更难预测了。帝国政府对于每一问题,不得不尊重那最表现离心力倾向的自治领的意见。意大利的帝国扩张,使她须要一次而永久地脱离英国的“友谊的”羁绊。墨索里尼在非洲的成功,以及意大利军备的扩充,是对英帝国的生存利益之直接威胁。反之,在德国看来,她同意大利的不可靠的友谊,乃是在较远的将来是为争取英国善意中立[注:指取得英国的中立。——译注]的斗争之一个手段。德国在其争取世界霸权的途程中,如果放弃这一阶段,就只有同苏联订立协定。这种情形并非不可能,但它只成为第二等的和后备的计划。希特勒之反对法苏同盟,并非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原则的仇视(没有一个认真的人现在还相信斯大林的革命作用),而是因为她要不受束缚地的能同莫斯科订立协定以反对巴黎,如果她同伦敦协定反对莫斯科不成功。就是法苏协定,也不是稳定的因素。她和旧日的法俄军事同盟不同的地方,就在她是混沌的一团。法国的政策经常的依赖英国,常在有条件地和德国接近及无条件地和苏联友好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摇摆的态度是愈来愈增大的。
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形势还要复杂,他们很像天上的卫星,不知道围绕着哪一个行星旋转才好。在纸面上,波兰是和法国同盟的,但事实上是同德国合作。罗马尼亚形式上是加入小协约的,然而波兰拉她到德意影响之下,则颇有成功。贝尔格莱德[注:南斯拉夫的首都。——译注]和德意的日益接近,不但使布拉格[注:捷克斯拉夫的首都。——译注]而且使布加勒斯特[注:罗马尼亚的首都。——译注],日益不安。从另一方面说,匈牙利完全有理由害怕她的收复领土的欲求,成为柏林罗马和贝尔格莱德间的友谊之下的第一个牺牲品。
大家都要求和平,尤其是从战争得不到一点好处的国家,巴尔干各国,波罗的海各小国、瑞士、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他们的阁员出席各种会议,成立协定,发表和平演说,整个的说来,都像火山喷口旁的傀儡喜剧。任何小的力量想旁观是不能够的,一切国家都要流血,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会相互作战。在昨天看起来还是荒谬的思想,今天已经是成为可信的了。只须德国支持瑞典,英国支持丹麦,斯堪的纳维亚的“姊妹”国家就要跑到敌视的阵营中——这自然以英德间的战争为条件。
美国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离开欧洲的纠纷更远一点,在一九一四年她也是如此。要成为一个大的强国,特别是最大的强国,想不受一点惩罚是不可能的。下命令保守中立要比在实际上维持中立,更容易些。何况除了欧洲以外还有远东哩。把大多数列强都弄得没有办法的在世界工业恐慌的那几年内,日本就彻底地夺取了满洲,占领了北中国几省,威胁着要更进一步去分解这一伟大的和不幸的国家。苏联的内部政治危机,红军的领袖之被枪决,以及莫斯科对于黑龙江小岛问题的可怜的屈服,这些都最后地使日本军阀敢于肆无忌惮。现在是整个远东的命运问题。
华盛顿政府正在改变路线,舰队在太平洋的集中,五万架轰炸机的制造,太平洋空中的发展,太平洋群岛的设防计划,非常明显地表示出她准备放弃自愿的孤立政策。但是在远东,我们还不能确定地预言,将来各种势力要如何联合。日本对英国提议在华合作,想逐渐地缩小英国在华的势力范围。然而英国在接受或拒绝这个提议之前,要先扩张她的海军,强固她在新加坡的根据地,并在香港增防。英国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还是不确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军事同盟的形成比军事冲突的成熟要迟缓得多。
“等待观望”(wait and see)的政策之还有意义,只是因为在欧洲分为两个阵营之前,英国的特权还能保存。但是当一切的国家无例外地不得不学习使用待机卖友的方法的时候,外交关系就变成了无意识的把戏,其参加者就像捉迷藏似地,拿着手枪互相捕捉。大大小小的国家似乎只有在新的大战的第一炮响了以后,赶快的建立军事同盟,此外没有旁的办法。
和平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形形色色的和平主义者在不久以前还相信或装着相信借国际联盟,堂皇的和平大会,人民投票及其他戏剧的表现(多数是由苏联的预算项下付款的)之助,可以防止新的战争。这些幻想有什么结果呢,七大强国中有三个,美、日、德,是在国联以外,第四个强国的意大利,从内部毁坏国联,其他的三个国家,则一天天地感觉不需要国联的商标去掩盖自己的利益。日内瓦机关的忧伤的拥护者,昨天还称呼它是“人类的希望”,今天却得出结论说:挽救国联的方法就是对它不要提出严重的问题。一九三二年,当有名的军缩会议开幕时,欧洲的军队是三百二十万人,一九三六年则增加到四百五十万,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薛西尔爵士的人民投票的主张怎样了呢?最近一次的诺贝尔奖金应该给谁呢?日内瓦的军缩的政策,甚至已不成为讽刺画的良好题材了。
新的狂热的军备扩充的主动者,是法西斯的德国,由于她的无误的本能,伴着喧闹的疯狂,她得以解除了凡尔赛的锁链。但新的世界冲突之不可避免,是在英国的例子中最可信地表现出来。这一个国家之保守的和平主义,直到最近期间,是靠尽可能地少花费以保护旧的赃物的信念来维系的。然而英国的政策在满洲、阿比西尼亚、西班牙的降低身分的失败,告诉鲍尔温及其同事们,专靠旧日力量的惰性是不能生存长久的。由此,就发生惊惶的自卫的意识,这表现在最大规模的军扩计划中。英国准备在最近几年内,在海上与空中成为最大的强国,这都是为了和平为了维持现状!然而她对于大西洋彼岸的海空军的军扩,给了不可制止的推动。这就是吃得最饱的“和平的”“民主的”和领导着军缩会议的国家的道路:由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由和平主义到扩张军备。地球上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由扩军走到战争呢?
我们能不能期待从下层,即工人群众,用总罢工、暴动、革命的方法,对于战争的危险给以抵抗呢?理论上说这非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把愿望或者恐惧当事实,那么这一前途,我们应该承认是很不可信的。全世界的劳苦群众,在意大利、波兰、中国、德国、奥国、西班牙,部分地在法国,以及许多小国中,受到了可怕的失败,而他们现在正被这失败所压制着。旧的国际——第二第三和职工国际——和民主国家的政府正在紧密联系着,从事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准备。固然对于德、意、日三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都是失败主义者,但这只是表明,他们只在他们没有任何势力的国家才作反战的斗争。为了能在反军国主义中抬起头来,群众须先摆脱这几个国际的羁绊。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不是一天或几个月所能解决的任务。现在无论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比新的战争之准备,要来得慢些。
为了辩护自己的军国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政策,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宣传一种思想,彷佛新的战争将有保护自由和文化,抵制法西斯的侵略者的使命:一方面——“和平的”国家,为新旧大陆的民主大国所领导;另一方面——德、意、奥、匈、波兰、日本。这样的分类,即就纯形式方面来考察,也是使人怀疑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同是法西斯的国家;罗马尼亚不见得比波兰更接近民主主义;军事独裁不但统治着日本,而且统治着中国,斯大林的政治体系一天天地更接近于希特勒的体系;在法国,甚至在新的战争发生以前,法西斯主义有可能扫除民主主义;无论如何“人民阵线”的政府尽了它的一切可能在帮助着这一转变。我们看,在现在的世界体系中,狼和羊的分别并不如此容易呵!
至于民主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如何呢?我们与其推测将来,不如看一看比利牛斯半岛的情形。首先,民主主义对于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施以封锁,理由是不给意德以干涉的借口。但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无需何种借口而实行干涉时,“民主主义”又赶忙地为了和平的利益而屈服在干涉之前。西班牙的互相残杀正不得开交,而民主主义的代表们却为将来应用哪种不干涉方法的讨论所吸引。莫斯科政府企图用急进的装模作样,以掩饰它对于可耻的有罪的政策之参加——这种政策帮助了佛朗哥将军的工作和巩固了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的地位。——但这掩饰是徒劳的。决定西班牙与别国的将来关系的,不是政治的原则而是她的丰富的矿产。这对于将来是痛苦的教训,然而又实在是无价的教训。
以上所述的国家的分类,固然有其历史的意义,但这意义完全不是像不值钱的和平主义者的抄本上所写的那样。那些国内矛盾已达到最尖锐点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原料,没有世界市场上充分的出路的国家(德、意、日);那些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国家(德、匈、奥);最后,那些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已被前资本主义的残余所复杂化了的国家(日本、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都要首先走到法西斯主义。一切这些历史上进步迟缓的或者受屈的国家,自然最不满于我们地球上的政治地图。所以它们的外交政策,比那些有特权的国家——首先关心于保护从前所掠得的赃物的国家,更带侵略的性质。由此就发生了拥护现状与反对现状的两种国家的区分。这种区分是很相对的。并且法西斯的与半法西斯的国家,主要的是在后一集团中。但这并不是说,正是这两个集团将来要互相作战;世界冲突发生的时候,拥护现状的政纲要毫无踪迹地消灭。因为这是新的世界分割的问题。现在反对维持现状的法西斯主义者,将来在作战的两个阵营里都会有。因为同盟者的选择,不是决定于政治的同情,而是决定于地理的形势,经济的联系,尤其是决定于力量对比的估计。希特勒将会很欣喜地去联合英国以便从法国夺取殖民地,即使因此而同意大利的法西斯作直接战争亦所不惜。墨索里尼一方面可以“背叛”而且多半要背叛希特勒,正如一九一四年意大利背叛霍亨索伦与哈布斯堡[注:德、奥的王朝。——译注]一样。“神圣的自我主义”将在法西斯国家间的关系中奏其凯旋。
固然,独裁主义的国家,是最适合于“独裁的”战争本性的制度。但这只是说,现在的民主主义在世界战争的过程中,或者甚至在其前夕,必然要接近于法西斯的政制,假使不是完全让位给它的话。然而政治体系的接近并不含有敌对的利益互相调和的意义。法西斯的法国多半不会和希特勒分配自己的殖民地;假使穆斯莱爵士[注:法国法西斯派首领。——译注]在英伦三岛取得了政权——历史上说来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他也不会比现在的英政府更倾向让意大利支配地中海。总之,战争的阵营的构成,以及战争本身的进行,不决定于政治的,种族的或道德的标准,而决定于帝国主义的利益,其它的一切都是向我们的眼睛中撒灰尘罢了。
战争何时发生
加速和延缓战争爆发的势力既是如此众多和复杂,因而企图预言战争发生的日期似乎太是冒昧,然而现在有几点可作为预测的根据。伦敦的人们倾向于估计最危险的时期到一九三九年完结,那时候英国预先指定为保护“和平”而扩张的军事力量,将达到充分的高度。从这一观点说,战争的危险是和军备的扩张成反比例的。
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不会在这种形势下利用剩余的有利的时间,在最近的廿四个月之内挑起战争吗?许多地方使我们相信,不会的。决定的不是意大利而是德国,然而德国没有准备好。固然,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活的传统,在德国的高的技术水平之下,可以使希特勒以历史上空前的速度进行准备的工作。然而就是最有威权的政府也不能创造出奇迹来。从凡尔赛和约成立到国社党胜利之间的几年间,德国的青年并未服过兵役,国内也没有现成的后备军。要想使几百万人受最简单的军事训练,必须有众多的军事干部和下级官佐。创造最完善的军事机械,并大量生产它,储蓄必需的原料,教育新的指挥干部,对于人民施行军训——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正是由于希特勒的军事机关之庞大地扩张,所以在每步上一定都要暴露出不平衡和缺点来。德国的当局比它的反对者估计它的军事准备,多半要低得多。至少还须要二年,然后柏林的参谋部才不至于阻遏其政治领袖的不耐。
然而军备的状况只是爆发战争的一个因素,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一切的国家,都感觉到自己已“充分的”武装起来的时期是永久没有的。自然,军备的扩充,就其本身说来,是走向战争而不是走向和平,但军队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又是物质利益的工具。挑起新的战争的因素,多半将由经济景气的转变来供给。
我们回忆一下:长期的工业繁荣,在一九一三年为经济恐慌所代替。这一恐慌不但是周期性的,而且也是属于结构上的。欧洲的生产力已经在民族国境的范围内感觉了束缚,一九一三年的恐慌便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焦虑,于是他们很快地就失去了期待和谨慎。结果在一九一四年就发生了战争。固然最近一次的恐慌(一九二九~三三年)没有引起军事的震动,前此一阶段的繁荣产生了极其盲目的乐观,使统治阶级坚信,恐慌只不过是一时的衰落。但贸易日渐停滞,失业军不断增加,于是这种幻想也逐渐消灭。那几年的外交政策——除了最受痛苦的几个国家(日、德、意)以外——都是期待的,不坚决的,和萎弱的。
新的恐慌的到来(就所有的资料看来是不远的),对于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将起完全不同的作用。现在的经济景气——在世界市场的混乱,货币制度的破坏,长期的失业的状况下——任何人都不相信是会支持长久的。这一景气主要是由于军事定货而得以维持,它的意义只表示经济基础的实质耗损。因此,它正准备着新的,更深刻的和病态的恐慌。统治阶级对于这一点,现在不能不明了。军备扩充计划的执行满期愈近,命运主宰者们的幻想将更少,他们将更焦急。
但是,统治者有没有可能来延缓这种恐慌之到来呢?或者,更重要的,他们有没有可能把它约束到很短的时期内,使它不致引起社会的震动呢?要实行这一点,至少要撤去关税壁垒,恢复金本位,调整国际债务,并提高人民的购买力,使扩充军备这机构走上相反的方向。只要不是盲目的人,就会同我们一致地承认:这类的奇迹的希望是没有一点根据可以实现的。
本年六月底,四十个国家的商业代表,在柏林集合,听戈林对于奥太基[注:即一国经济自足主义。——译注]的赞美诗。各个代表论自由经济制度的优点的演说,只是对于现实的嘲笑。原料丰富的国家是否愿意在战争时期给她的反对者以保障呢?殖民地的帝国是否愿意将一部分的领土送给受屈的国家呢?集中黄金在手的国家是否愿意不自私地医治其劲敌的已破坏的货币制度呢?这些简单的问题自身,已具备了现成的答案。国家的壁垒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愈反动,则现在各国政府更要不惜牺牲一切地来保存它。并不是各人都公开地对于奥太基唱赞美歌,但是人人都努力藏在它的幻影之下,而且,“奥太基”并不是在国境内自给自足的意义;正和德意的纲领所特别坦白表示的,奥太基需要夺取殖民地和一般的别国的土地,闭关的经济学说只是帝国主义侵占的前提。
从经济困难所生长出的战争危险,更增加了这些经济困难。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绝交,正式宣战,和尊重中立,是和十六七世纪所盛行的女裙和跳舞一样,早已完全过时了。每个政府都在警戒着。和平时期的紧张状态(此种紧张状态此刻采取着从前在绝交以后才有可能的那种形式)并不能促进经济的繁荣。一切都指出将来的危机要大大超过一九二九及其以后几年的危机。消极等待的外交,在这些条件之下是不可能的,用美国这样流他人之血的政策,欧洲是行不通的。新的危机将尖锐的提出一切问题,并推动统治者采取坚决手段,这些手段不能和失望一拚的手段有什么不同。
由此看来,最近三四年终了的时候,换言之,正常扩军计划已经完成,而准备着“保障和平”的时候,战争或者就要爆发。自然,我们所以要指出这个日子,只是为着便于估定路向,政治的事变可以加速或迟延爆发的日期,但是爆发的必然性已潜伏在经济的动态,社会矛盾的动态,以及军备的动态之中了。
未来战争的战略
一九一四年的前夕,占支配地位的学说是迅速的歼灭战。这一学说使法国受到了特别大的牺牲。“歼灭”延长了五十二个月。在人类作恶的天才发明了无比锐利的屠杀机械以后,用这些机械武装起来的军队,像掘土鼠一样在深掘的地中生活者。在大战中,战壕对于军事行动的束缚愈厉害,则凡尔赛和约以后军事学说中要摆脱这种束缚的思想便越勇敢。对于战略的轻视,及因相互屠杀而消费掉的天文学上的数字,这些都推动军事的空想家去找寻更光辉的和廉价的道路,于是便发生了新的学派:一派想用人数不多的技术的精兵代替武装的人民;另一派想将作战的中心放在空中;第三派寄托希望于死光。富莱耳将军认真地相信,在战争中使用电力,能“去掉过去一切战争中的第一个弱点,就是人的因素”。塞克特将军[注:德国将军。——译注]得出的结论是:在人群与技术的竞争中,胜利属于技术。由此发生一种理论,就是人数很少的技术的精兵部队,以铁流与火光侵占敌人的国家。其实“技术”和“人群”的对立,和有时说的“质”与“量”的对立一样,只是一种无生气的抽象。假使有二十万的机械化部队能作成奇迹,那么两个这样的部队所能作的,将不是二倍而是四倍多的奇迹。数字的法则,就是在最高的技术基础上也有效的。简单点说,战争的国家不得不尽可能地动员最好的武装兵士之最大数目。因为如此,我们就说不能希望“迅速的歼灭”。
赛克特所提出来的少数军队的学说,不是导源于军事的物质条件,而是由于德国为凡尔赛和约所限制的条件。当这些限制摆脱了的时候,希特勒就实行征兵制。英国的传统和财政都妨害义务兵制的实行,于是理论家想以机械代替人;然而大战的第一天,在英国也是实行征兵制的第一天。
罗马和柏林的军事家,都以空袭的前途安慰自己或人民。这种空袭,想以一击破坏敌人的生活中心。这种学说的来源,就是因为罗马和柏林都没有汽油和黄金,可以支持长期的战争。戈林很夸耀将来的空袭的光荣,以及自己的防空工具,说这种防空将打断敌人实行空袭的愿望;但不幸别的国家也能与航空平行,发展防空的设备。空中的决斗可以产生重大的策略的成绩,但在战略的决定上是没有作用的。
还有一个希望:用一种异常的技术的“秘密”,可以立刻倾覆未及准备的敌人。这种希望也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每一个新的发现,都同时刺激起发明家的思想。军事的技术比其它的技术更带国际性,这一点正是军事工业的公司和间谍们所充分注意的。参谋部所有的秘密,是对于自己人民的秘密,但没有对于别国的参谋部的秘密。
任何军队都不能把现成的化学的与电气的奇迹储藏起来,每一个发明都要在实际上经过试验。而这种试验,只有战争才能给予。军器的大量生产的设备,需要一年或甚至二年才能完成。单靠这一点,我们就可说,在上次战争中所没有试验过的任何“决定的”技术手段,我们都不能期待其被广大地使用。将来的战争是用上次战争完结时的那种水平来开始。新的手段将逐渐的和旧的相联合,使军队更其繁重和人数更其众多。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中,生产的范围受人民的购买力的限制,机械在相当的水平上排挤人工。军事中可没有这种限制。人们相互屠杀,不顾及他们的“购买力”如何;现代的军队虽然有机械的运转,但还是同拿破仑时代一样,需要每三个人有一匹马。就绝对的数字说,这就需要几百万的马匹。同样的,虽然军队的各方面都在机械化了,但服务于机械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最近时候的军事行动(远东、阿比西尼亚、西班牙),虽然是零碎的,但仍足以将战略的思想从天上送回地下。战争的危险愈逼近,官式的战略愈须回到已被试验的方法。现在,一切海军强国,都忙于旧军舰的改装和新的大军舰的建造。这种新的军舰在大战以后的头几年,是会被人们视为太古时代的鱼龙一类的东西。很可信的,钟摆在此地是摆回去得太远了。在海军中,机械是专制地统治着人,战略的思想特别保守,不容易转动。
无论关于无畏舰的情形是怎样,英国不得不重新在欧洲大陆上防卫自己。人不是生活在水上,也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上,海军和空军只是侵入敌人领土或防卫自己领土的辅助工具,战争的命运还是决定于陆地上。陆军无论在欧洲或世界的范围中,都是进攻或防守的主要力量,军队的基础是步兵。别的条件如果相等,则陆军的人数愈多,胜利的机会便愈大。
战争将带有整个的性质,这不仅从在地上、地下,水上,水中和空中同时展开行动的情况上表现出来,而且从战争将一切人民,富源,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都卷入它的漩涡的情况上才表现出来。一部分的人民将作战于立体的前线,另一部分的人民将“后方”制造军火,饥饿和死亡。虽然已经征服了以太高气层和北极,虽然有死光和其他的恐怖,但军队将和上次战争时一样地坐在污泥中,或者还要深得多。
自然,还有各国的经济的技术的水平之区别,文化较高的优点在战争时期特别表现的有权威。假使“秘密”被一切的参加者都知道了,那么此种秘密的大量生产的力量还是不等的。然而水平的差别,和在上次战争中一样,将大大地为作战双方的几国的集团所中和化。例如,德国对于法国的太明显的优势,假如表现在事实中,将引起英国方面的加倍努力;同时,或者会使意国恐惧,而采取静观的态度,甚至接近法国。又如德国军事的技术的优势在与英国斗争中获得了重大的胜利之时——或者相反的——美国便不得不脱离期待的中立的状况。我们地球上各部相互依赖太大了,不能希望军事的冲突之局部化。无论战争在什么地方,以什么理由开始,一个大强国的重大胜利,不是战争的完结,而是战争区域的扩大。对于□利者的恐惧,会引起敌对联盟的扩大。战争的螺旋线必然要波及到整个的地球。唯一的中立的地带,或者是南极,而北极则无论如何将成为军事飞行的根据地。世界战争如果任它以自己的逻辑发展,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之下,只是人类的一种复杂的和代价很大的自杀方法。这一目的可以用别的更简单的方法去达到,就是把全人类都关在笼子里沉入大洋。这一“迅速的歼灭”是现代技术所完全能够胜任的,并且无疑地要比任何列强的扩军计划便宜些。
战争与革命
在战争中强大的国家比弱小的国家占优势,地理的形势,土地的面积,人口的数字,原料的来源,黄金的储备以及技术,都保证美国比其他各国要占极大的优势。假定任世界战争自然地完结,换言之,就是战争的双方完全衰竭了,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统治我们地球的,将属于美国。然而美国对于没落和破坏的国家,对于饥饿、瘟疫和野蛮的国家的统治,必然也是美国本身的文明之衰落。这种前途的现实性是怎样呢?由于新的战争的结果,人类的长期衰落,并非不可能,但幸而这不是唯一的前途。在各民族的互相屠杀之自然结束以前,每一国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要受严重的试验,革命可以切断战争的进行。
上面说过,我们不大希望无产阶段,能在任何一分钟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住战争的爆发。相反的,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以及在战争的初期,群众中“国家的”向心的倾向和爱国的影响将盛行,这无论是在一国内的各阶级和民族,或是在英帝国的各部分,都是如此,然而随着军事行动发展,则伴着它而来的贫困化,野蛮和失望,一定不仅将使一切的摩擦对抗,和离心的倾向复活,而且将使其尖锐化,这些倾向迟早将以暴动和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然战争即在此种情形下,也要使人类陷于前所未有的痛苦。然而民众结束战争愈早,则人类医治它所受的伤痕亦愈容易。然则从这观点看来,未来战争的时间将延长多久呢?
因此新的战争既是从旧的战争完结的地方开始的,则在下次战争的初期,人类生命之牺牲及战争的物质耗费,一定要比过去战争开始的牺牲与耗费高几倍,而且其趋势是迅速增加的,速度将是狂热的,破坏将是更大规模的,人民的痛苦将是更不可忍受的。所以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民众的反作用不会像在沙俄时代那样需要经过两年半,像在德国及奥匈之须经过四年余,而是要快得多。但是只有事变自身才能给时间问题以最后的回答。
在此种情形下,苏联将有如何的前途呢?西方官式舆论,对于苏联及红军的估计,有过几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五年计划的混乱,使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比重,几乎等于零。后来,工业的进步,尤其是军事工业,与世界的经济恐慌相对照,大大提高了苏联在世界的威信,法国之害怕德国的复仇政策,使苏联外交能成为欧洲政治中不可轻视的因素,红军的威信一天天地增高起来。然而这没有延长好久。清党肃军的流血,是受了统治的党派的指使,由此使优秀的军事领袖被屠杀,这在到处都引起尖锐的反感。苏联外交在关于黑龙江小岛问题上的屈服,使日本得以放胆进攻中国,同时使伦敦对巴黎常进忠告:不要希望莫斯科,请与柏林订立协定。然而今日对红军之轻视的估计,正如昨日对斯大林统治之不可动摇性的信仰一样,都是片面的。造谣的污蔑和对昨日的偶像之枪决,自然使军队的行伍中,有点动摇和颓丧。然而阅兵和演习在外国军官面前所表现的苏联兵士及官佐的忍耐,活泼及应变等特长,仍然是一种现实,正如苏联的坦克车飞机的品质优良,及苏联飞行家的勇敢和艺术高超,是一种现实一样。此种破坏国防的流血的肃军,首先表示出寡头的统治者已和人民(包括红军在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的尖锐性正证明,国内经济的和文化的极大进步已和斯大林的政制益难调和。苏联的政治革命,即推翻腐化的官僚层的革命,无疑地将是战争之最近的后果。一切都使我们相信,只要全人类不退到野蛮时代,则苏维埃制度的社会基础(新的财产关系及计划经济经济),将经得起战争的试验,甚至在战争中还能强固起来。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可预先定一不变的法则:就是那些土地问题没有及时的获得民主的解决,封建的残余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它们的政治制度将在战场上首先被牺牲。世界强大的锁链中之最弱的一环,这次是日本。它的社会制度——如军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及凭借在半封建之上的野蛮状态——受到战争的打击,将为极大的社会变化所推翻。第二三等国家中最危险的是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这些地方的农民,实质上说,还未脱离昔日的奴役。
其次轮到的是法西斯制度。法西斯主义之在国内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中取得了政权,不是偶然的。固然在军事及外交领域中,独裁的国家比民主主义的繁重机构有极大的优点,首先是手腕自由,不受内部抵抗的束缚的优点。然而这不是说没有抵抗。抵抗只是处在隐藏的状态中,而且在暗中集垒起来,直到爆发的时候。在德国和意大利,粮食和原料的缺乏,陷群众于不可忍耐的痛苦,假使在战争初期,这些国家能有或将有重大的军事胜利,则在第二阶段,它们比自己的敌人将更早些地成为社会震动的园地。
差别的只是时间。战争要将各国的制度变成同样的情形。各国的经济都要隶属于国家的统治,军事的检查,和过去一样,也是政治的检查。反对派将被压倒。官式的说谎将享有独占的权利。前方和后方的差别消灭。军事法庭在全国各地都成立。各国所有的军事储藏和原料资源的差别,将较政治的原则的差别,要现实的多。
法国的世界地位,(为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无论如何和该国的实在的资源不相符合,它的人口没有增加,经济也是停滞,它没有自己的石油,它的煤的储藏也是不充足的,财政是不稳固的。法国的国家安全,比其它任何国家更依赖于别国:依赖英美,假使不是苏联。战争将把法国变成第二等的强国,随着国家的世界地位的动摇,它的社会制度也要动摇。
英帝国的离心力倾向,是宗主国的现实的强大力量和它的历史的遗产两者间之不相称的结果。宗主国的大规模的扩军,是想告诉殖民地和自治领,它单独地就能保障它们不受侵犯。保护帝国的支出,比由此种支出所得到的利益,要增加的快些。这样的经济,必然会走到破产。新的战争将使英国削弱和分解。帝国力量的崩溃,又开辟一社会震动的时代,战争对于任何一国,都不会无踪迹地过去。在痛苦痉挛之中,全世界要改变自己的面目。
我们的预测看起来是很暗淡的,这不怪我们;在我们的时代的调色板上面,我们找不着粉红的颜色。我们努力从事实,而不是从自己的愿望,得到结论。斯宾诺莎老头子教我们不错:“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科约阿坎。